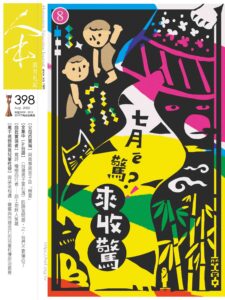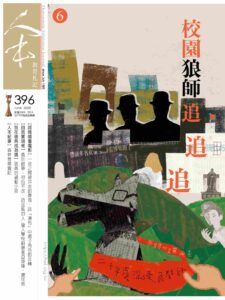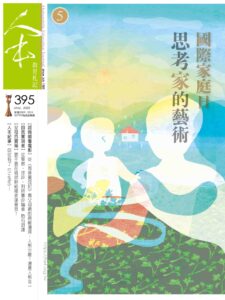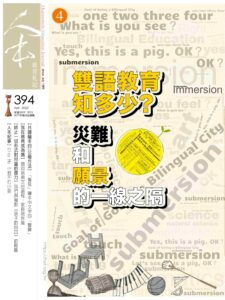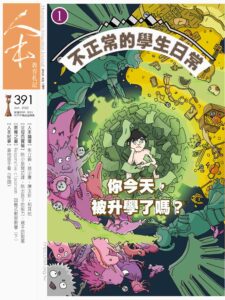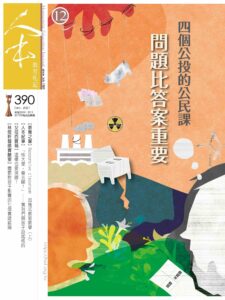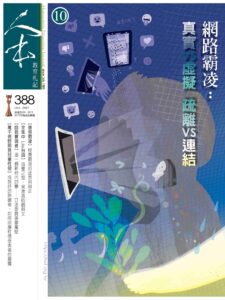森小的一堂 國語課:風箏(下)| 人本教育札記
森小的一堂 國語課:風箏(下)

哥哥不僅不准瘦弱多病的弟弟放風箏,甚至當弟弟躲起來「苦心孤詣地來偷做沒出息孩子的玩藝」,哥哥竟然闖入,一把扯壞、踐踏快做好的風箏,還「…傲然走出,留他絕望地站在小屋裏」。哥哥完全無視於弟弟的絕望哀傷,一個趾高氣昂的小霸王,作者在這段最後留下一句:「後來他怎樣,我不知道,也沒有留心」。
「他為什麼不去跟他哥PK?」孩子忿忿不平的握緊拳頭。
「上一段已經說弟弟很弱小了啊!」另一個孩子慢條斯理說著。
「可以拿棍子啊!就算打不贏我還是會打回去!像我姊就會很慘,會被我媽媽罵。」孩子在自己的情境中,堅決抗暴。
我凝視著孩子,遙想著魯迅那一代和這一代,台灣真的不一樣了!孩子無法想像,上一代的爸媽介入,會更好嗎?如果會,這哥哥又為何如此惡行惡狀?這一切我無法在三言兩語中說明,先循著孩子的思路問:「地上應該有工具,為什麼弟弟不拿起來攻擊,例如…剪刀?」
「如果弟弟攻擊,會被哥哥搶過去。」另一個孩子幫忙回答。
我請大家回到文本仔細看,在魯迅的筆下,爸媽終究缺席了,弟弟完全的孤立無援。
「弟弟很慘。」孩子悲哀地說著。
既然哥哥這麼趾高氣昂,為什麼最後還要加上:「後來他怎樣,我不知道,也沒有留心」?作者想表達什麼?
「弟弟死了嗎?」孩子又問。
「弟弟應該活著…他想掩飾?」另一個孩子接著回答、追問。
「我想,他真的沒有留意。他當時不care…」
孩子們一人一句自己討論了起來。我聽著,微笑,只跟了一句:「當時不care,現在呢?」
「現在很care。」
「我覺得,弟弟可能不理他了。」孩子斷言。
聽孩子斷言,我請他們猜猜看,故事再來會怎樣?孩子們的猜想有:弟弟再也不放風箏了、繼續過日子、表面不放風箏但是內在洶湧、做什麼都躲著哥哥。
結果,孩子們閱讀後,發現跟自己猜想的完全不一樣,興致更濃烈。哥哥說:「我的懲罰終於輪到了」!他在中年時吸收西洋新知,恍然大悟「玩具是兒童的天使」,對弟弟「精神虐殺」的這一幕終於從記憶底層湧現。

我故意問:「為什麼不寫『我的懲罰終於到了』,而是我的懲罰終於『輪』到了?為什麼作者要用『輪』呢?」
「因為之前是弟弟啊!」孩子一語中的,完全捕捉到魯迅遣辭用字的心機。從他們雲淡風輕的回應,感覺他們認為自己沒什麼了不起,但我知道,經過這幾天課上的唇槍舌劍,孩子們的語文敏銳度躍升一大步。
中年的哥哥想跟弟弟道歉了。哥哥想了兩個補過的辦法,其一是兩個中年大叔相約一起去放風箏。孩子笑著問:「他知道自己幾歲了嗎?」魯迅當然知道自己幾歲了!所以他還想了第二個方法:
我也知道還有一個補過的方法的:去討他的寬恕,等他說,「我可是毫不怪你呵。」那麼,我的心一定就輕鬆了,這確是一個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們會面的時候, …我便敘述到這一節,自說少年時代的糊塗。「我可是毫不怪你呵。」我想,他要說了,我即刻便受了寬恕,我的心從此也寬鬆了罷。
「哎喲!他加了一個『罷』,就是不可能的意思!」孩子說得輕盈,我大吃一驚。這個點是我備課時完全沒想到的,孩子自己看出來了。我還來不及好好稱讚,另一個孩子問:「小何,我是不是猜對了?弟弟是不是跟他講不怪他,但是其實還是沒原諒?」
孩子們的心思真靈活,源頭活水不斷冒出來,和我小時候傻傻在課堂上聽講、發呆的光景完全不一樣。一群小人兒已經開始猜想:弟弟的反應。
「我覺得弟弟會原諒他。」
「蛤!我覺得弟弟會說,我不原諒你!」
「他會原諒他,只是他心裡沒真正放下。我是說,哥哥心裡還是放不下。」
「也可能他覺得自己很敷衍,所以他也會覺得弟弟也很敷衍。」
課堂上,大家熱烈猜想著。下課鐘響,有人高喊:「不要下課!」於是,我發下下一段,沒想到不到一分鐘…全班陷入混亂!
「有過這樣的事麼?」他驚異地笑著說,就像旁聽着別人的故事一樣。他什麼也記不得了。
「他不記得了!」幾個孩子反覆說。
「好可憐的哥哥!」
「也好可憐的弟弟!」
「挖靠!八點檔!」
「拜託你記得啦!拜託你記得…」
「白對不起了…」
我問孩子們,弟弟真的不記得了嗎?是真忘記,還是假忘記?
孩子們又陷入一陣混亂,是在討論。多數人說:「怎麼可能!」「童年陰影,不可能忘記啊!」「假的忘記。」一位素來沉默的孩子終於開口:「他完全記得,只是不想記得。」
一個孩子甚至走上台前。「砰!」小手往白板一拍,大聲吆喝:「各位,你們自己想一想,如果你們小時候被哥哥或姐姐這樣對待,你可能忘記嗎?」
「我覺得他可能不想讓哥哥難過,結果哥哥更難過,好悲哀喔!」「假忘記派」孩子做了總結。
我看著一面倒的情勢,說道:「可是我剛才有聽到,好像有一個人覺得弟弟是真忘記。差異是珍寶,我們來聽聽她的想法,好嗎?」
那是唯一的孩子,她一邊想,一邊穩穩地說:「我覺得,弟弟不會笨到以為說自己忘記,就可以讓哥哥不傷心。多年的兄弟,怎麼可能不了解他哥哥。而且如果是假忘記,作者就不會寫『就像旁聽著別人的故事一樣』。」

弟弟到底是真忘記?還是假忘記?討論遇到瓶頸,再來怎麼辦?打住?還是說一句「大家說的都很有道理」,呼攏讚美一番?或者,我們就多數決,以投票決定:弟弟是假裝忘記?
時常有人誤以為開放式教育就是課堂熱絡討論一番就好,語文課更是「作者已死」,沒有答案。但是,在森小課堂,我們從不這麼主張。
我請孩子們先試著推想:如果弟弟不是說忘記,而是說很難原諒、或不想原諒,哥哥的反應可能是什麼?
「哥哥就會想,那不然就不原諒。」孩子沉思著說。
「對!你不原諒我,我也不用道歉了。對不對?好。再來想另一個,如果作者跟你們一樣,覺得弟弟不可能忘記,他可能會怎麼做?」我再問。
孩子們一片沉默。
「他可能會對弟弟更好,想讓弟弟安心,彌補,乞求原諒。是嗎?」
「同意。」孩子說。
談完不同的可能性,再請孩子們斟酌,「作者覺得」弟弟是真忘記,還是假忘記?請孩子們回到文本仔細揣摩,而不是只從自己的立場想。畢竟,以自己的情境作推想故然重要,但完全不考慮作者的情境,讀者就陷入「自我中心」或「腦補」,無法理解他人真正的意思。這對孩子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課。
為了讓孩子們仔細揣摩,那一周的回家作業,我出了一個寫作功課,題目是:「關於風箏,魯迅跟弟弟道歉這一段,作者認為,弟弟是真的忘記?還是假裝忘記?請在作文本寫下看法。」我附上了整段文章,請孩子們來回品味。
隔週,我一收到作業,一篇篇仔細閱讀體會,發現多數孩子還是陷在自我的情境,覺得「我不可能忘記」所以「弟弟不可能忘記」,而不是從文本推想「作者覺得弟弟是真忘記,還是假忘記?」。
對童稚的心靈來說,這真是困難的一課啊!我要放棄嗎?當然不啊!
我想了一個晚上,作了一個決定。在課堂上,我重新朗讀一次作業題目,然後一篇篇的讀著孩子們的申論文字,請孩子們先判斷,這篇是寫「我本人覺得」,還是「魯迅覺得」?
孩子們一篇篇的聽著,突然間,一個孩子大喊:「我寫錯了!我寫的是我覺得,不是魯迅覺得!」
啊!終於!經過這個覺察之後,我請孩子們重新閱讀文章,先讀完最後一段:
現在,故鄉的春天又在這異地的空中了,既給我久經逝去的兒時的回憶,而一併也帶著無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肅殺的嚴冬中去罷, ——但是,四面又明明是嚴冬,正給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氣。
再請孩子回頭斟酌:魯迅覺得弟弟到底是真忘記,還是假忘記?
「他已經不在乎冷不冷了,我覺得他是覺得弟弟真的忘記ㄟ。魯迅是那麼痛苦。他如果覺得弟弟是假的忘,應該會去找弟弟,跟他繼續講話。」原來堅持「假忘記」的孩子有了完全不同的見地。幾個相同立場的孩子,重讀也覺得弟弟「真忘記」了。
有意思的是,原來唯一主張「真忘記」的孩子說:「感覺他根本不在乎是真忘記或假忘記了,反正弟弟都這樣說了。他只能繼續痛苦。從文章看,魯迅就是覺得這件事無法真的了結,他永遠無法彌補了。」她又有了更深一層的看法。
「我覺得兩個都很有道理。」一個孩子說出我心中的想法,和感動。
「他弟有看到這篇文章嗎?」孩子繼續追問。
有看到嗎?我也不知道。關於魯迅和弟弟,外界紛紛擾擾諸多揣測,說不明白。關於這題,課堂上,我什麼都沒說。想著未來,有一天,孩子們自己會自己來告訴我吧!
如何給孩子更好的教育?為人父母/教師的您,是否正在追尋答案?進步的源頭,來自不斷的思索與釐清。《人本教育札記》多次榮獲金鼎獎、金蝶獎的肯定!國內第一本為家長及關心教育者所編寫的專業教育月刊,提供您看教育的不同角度。每個月都陪您,一步一步向前,充實自己。
- 本期特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