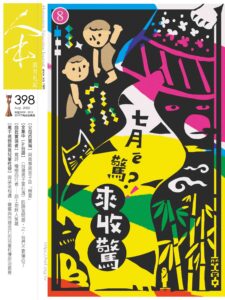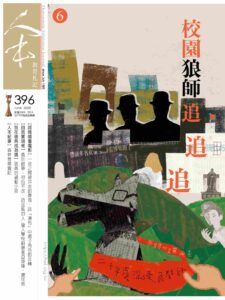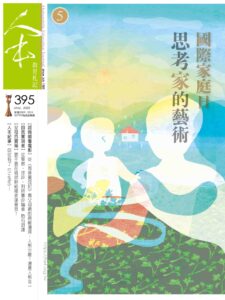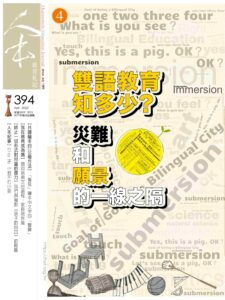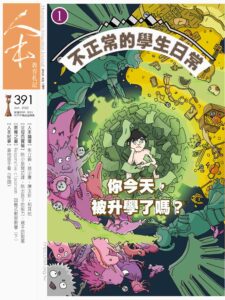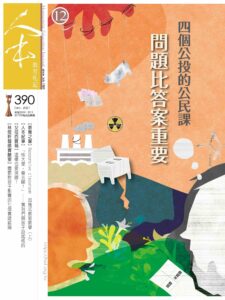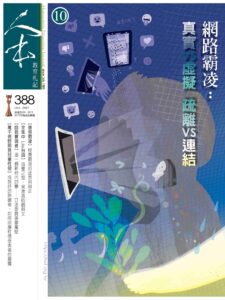森小的一堂國語課:風箏(上)| 人本教育札記
森小的一堂國語課:風箏(上)

「北京的冬季,地上還有積雪,灰黑色的禿樹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而遠處有一二風箏浮動,在我是一種驚異和悲哀。」
稚嫩朗讀的聲音剛結束,我正想開口講課,已經聽到來自四面八方的「回響」:
「作者住北京嗎?」
「為什麼寫『在我』?」
「為什麼寫『在我是一種驚異和悲哀』?」另一個孩子也問。
「『而』遠處有一二風箏浮動,為什麼作者這樣寫?」
我才要開始回答,一個聲音卻搶在我前頭,儘管他比第一波慢了半拍:「為什麼一定要說『灰黑色的禿樹枝丫叉於天空中』,這有什麼特別啊?」
這些「突擊」是在找碴,我卻覺得幸福。一個「活」的課堂,孩子們從來不是沉默被動的聽課者,他們才不管文章是魯迅、還是迅魯寫的,一無所知,也無所懼,一個個小傢伙們像大學問家,「問」得理直氣壯,且異常精準。這種時候我的腦中會閃過一個畫面:我,正在跟一群「劍客」比劍,唰!要從哪開始拆招呢?
劍客們武功高強,幸好我也是有備(課)而來:「對ㄟ!為什麼作者不寫『晴朗的天空中有灰黑色的禿樹枝丫』,而是倒過來。比比看,兩個句子的重點有甚麼不一樣嗎?」
「比較好聽?」一位優雅的女劍客說。
「兩個句子讀起來感覺不太一樣吧?試著把那一點點不一樣的感覺提煉出來。哪裡不一樣?」我向前踏一步。
「倒過來有寫詩的感覺。」浪漫劍客開口。
「先看到禿樹枝丫,到天空,然後看到遠處的風箏。」這位後發先至,正中要害!
作者確實運用了「鏡頭法」,帶讀者的視線先看到樹枝,再看天空,順著天空看到遠處有一二風箏浮動。「為什麼要說『在我』呢?你看到風箏通常是甚麼感覺?」我也不留空隙,忙著拆解下一招。
「我才不會驚異和悲哀!」「搞不好有人死了!」「這段文字有反常!」小傢伙們又此起彼落繼續唰唰唰。
諸位看倌們讀到這兒,是否感到有點不尋常。這位老師(作者)甚麼開場白、背景介紹、連引發學習動機的引言都沒有,就開始上課(文章)?對!多數時候我一上課就毫不客氣的切入正題,這是最快引發學習動機的方法。一部好的電影或小說不一定需要開場白,一堂好課也是,不必浪費時間和孩子們繞圈圈哈啦。

不只是開場,整個上課期間我也幾乎不和孩子們聊天話家常,那通常會把話題扯遠,我們非常專注在文章討論上,除非為了幫助孩子們理解課程、進入文章的情境,才說一點故事或玩笑。孩子們如果問了和課程無關的問題,我通常是說:「哦!你現在進廣告囉!這題我們下課再聊。」大人小孩相視微微一笑,繼續回到正題。
畢竟,比劍沒有人在聊天的!當然,鍛鍊思考,見招拆招不是爭輸贏,而是一起追究文章的言外之意,真正讀懂作者的心思。
魯迅的文字也讓人沒有失望的機會,他從第一段就在釣讀者的胃口,布局非常嚴謹巧妙,一段扣著一段。孩子們不斷追問,一直想往下讀,探究文字背後的玄機。
孩子們從「地上『還』有積雪」「『而』遠處有一二風箏浮動」「『在』我是一種驚異和悲哀」,已經體察出作者在冬日賞風箏背後,有一段不為人知的悲傷過往。他們不斷猜著:是誰死了嗎?當看到魯迅的「弟弟」出場,幾乎想斷言:「弟弟後來死了嗎?」!
弟弟到底有沒有死,魯迅沒說。他說的是,弟弟熱愛風箏,而自己覺得風箏是「沒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藝」,弟弟瘦弱多病,他不准弟弟放風箏,以至於弟弟「只得張著小嘴,呆看著空中出神。」而這一切在哥哥的眼中「都是笑柄,可鄙的」
「這段是『驚異』還是『悲哀』?」換我搶先出招。
「是悲哀!」劍客們不假思索。「他覺得自己做了可悲、可鄙的事。」
「你們也感到悲哀嗎?為什麼感到悲哀?」我追擊。
「弟弟瘋了,或,弟弟病得整天只在意風箏。哥哥覺得風箏很可悲,看到弟弟沉迷,也覺得弟弟很可悲。」自由的心靈正在努力的猜想。
「也說不定他後來想一想,覺得自己不應該這樣對待弟弟。」
「人生很悲哀!」
「他覺得自己很壞!」
悲哀來襲,孩子們陷入了漩渦,情感似水流,孩子們和魯迅的情感正匯聚交融,又流回各自內心深處,悲傷,深刻。
「弟弟為什麼不反抗?如果是我,我就會反抗我姊姊!」劍客不服輸,突然又醒來。
這是一個「活」的課堂,百分之百。
如何給孩子更好的教育?為人父母/教師的您,是否正在追尋答案?進步的源頭,來自不斷的思索與釐清。《人本教育札記》多次榮獲金鼎獎、金蝶獎的肯定!國內第一本為家長及關心教育者所編寫的專業教育月刊,提供您看教育的不同角度。每個月都陪您,一步一步向前,充實自己。
- 本期特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