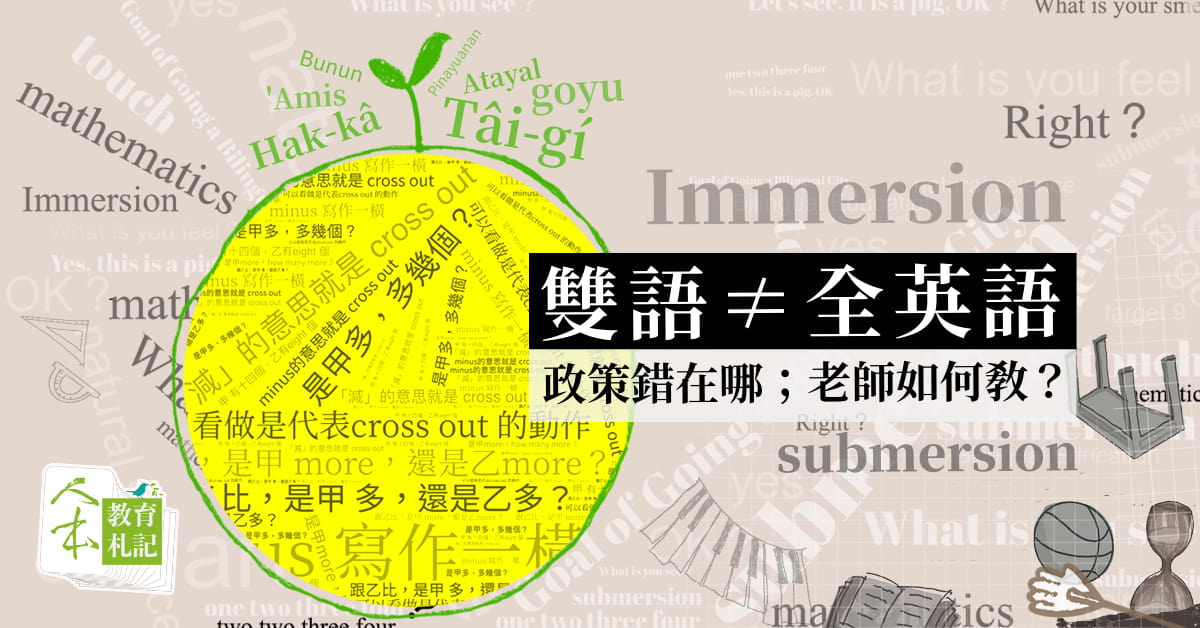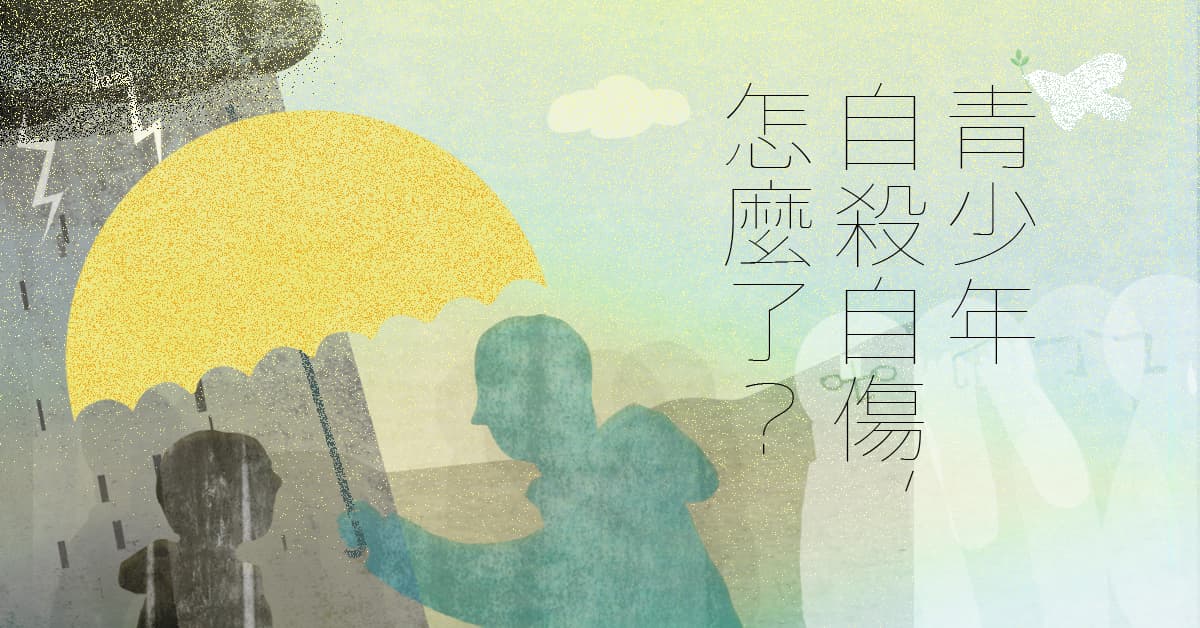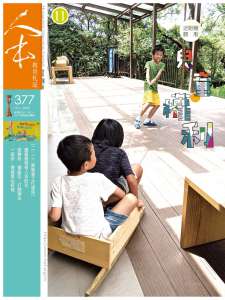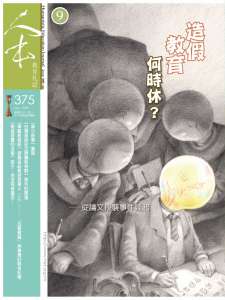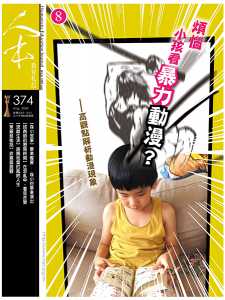專欄/國際島民
踏足國際,深入當地。時代流轉到二十一世紀,台灣的國際地位仍然模糊未明,而他國的故事,似乎總在遙遠的他方。 然而,一直有一群人們持續地從台灣出發,帶著自己的力量奉獻於遠方。而他們遇到了怎樣的故事,這些故事又如何讓他們重新理解他人與自己,乃至於我們足下的土地? 行過、走過,當故事越過海洋捎來音訊,就願他方遠方,皆非彼方。
—札記專欄【他方遠方都不是彼方】

「部分的總和不等於全體」你聽過這句話嗎?若要用一句話來詮釋我的工作,它將會是最好的寫照,時常浮現在我的腦海中。
國際志工,一個多麼熱血的代名詞,它象徵著國際間的交流,是一種移動力與適應力的養成,也是許多青年學子打開新一扇窗的媒介,終於有機會靠自己的雙腳走出台灣,去印證或推翻那些在課本上學到的知識,當你勇敢地將這一切都從口號轉變成實際行動時,你已然付諸它不一樣的意義。
關注我的臉書,大家常看到我南征北討在不同場合演講分享,談談這幾年國際服務的酸甜苦辣,語畢,多數聽眾總是爭先恐後問我:「你認為在國際志工的經驗中,自己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我相信,每個人在出發前都有對這個答案的預設,有人會說「施比受更有福」,也有人搶答「看見自己過得很幸福,學會珍惜」,不乏也有人全心投入去認識當地、體驗當地、愛上當地後,用情頗深說「這是一段值得珍藏一輩子的回憶」。每個答案都代表著國際志工之於自己的影響,請你們記得,這些涵蓋不同層面的詮釋,在人生的不同階段都有轉變的可能。
在我第一次、第二次擔任國際志工時候,也曾有過上面的這些感觸,不過如今,我已經是個往返台灣與海外頻繁的旅人,從過去的一個參與者角色,變成一個組織的負責人,自己上戰場當志工或者在身後擔任負責人的次數,也已經不是手指頭數得完,要我回答這題,我會說:「國際志工讓我短時間內壓縮成長,讓我知道部分的總和不是全體。」
隨心書寫至此,想要跟大家分享兩個小故事。
記得我第一次在海外做服務,以「旁觀者」的身分,協助同樣來自台灣的團隊在當地校內推動「環保回收」計畫時,我多麼投入,從規劃活動到校園落實,每一個細節親力親為,我們都相信著「只要善意付出,就會帶來或大或小的改變」。當地學生參與情形不如預期,在地的教師也在開會宣布時興致缺缺,這樣消極的態度一度讓幾位志工抱怨連連,開始自我質疑:「我們為什麼要為了這群不上進、跟不上環保理念的人們這麼拼命?」
在我還沒有找到理由反駁這些負面情緒前,志工終日的疲倦與老師們的放鴿子,成為壓垮表面和平的最後一根稻草,火藥味瀰漫著整個校園就要徹底爆發了,每個人氣得你一言、我一語講自己的委屈。試想:「為什麼一件好的事情,會受到這麼多的反對聲音呢?推動環保難道不好嗎?這可是國際趨勢哎!」
這時候,下課鐘響,我想迴避一下這個尷尬的氣氛,來到校內機車棚發呆,看著成群結隊準備放學回家的孩子,下一秒鐘,我看到幾位老師特意避開我的眼神,騎車呼嘯而過,回神看到他們車後載著大袋的寶特瓶回收,路過的學生見我看得離奇,笑著補充說:「老師是要帶回家去變賣賺外快」。那一瞬間,我心裡明白兩件事情:有人認為老師的形象,怎麼會做資源回收?那是因為我們活在台灣的價值認知中;有人認為老師的消極,怎麼會值得優秀的志工沒日夜的付出?那是因為很多時候我們「認為的好」,無故排擠到他們的既得利益。
我明白,人們總是喜歡在兩者之間糾結,一個是「眼睛看見的」,一個是「心裡相信的」,當兩者吻合時,順行無阻,當兩者衝突矛盾時,我真心奉勸不要急於下任何定論,因為很多誤解就是源於你不了解。
好幾年過去了,這件事情一直埋在我心中,我常以此奉勸志工夥伴在規劃課程、活動,甚至更大規模的專案前,多想想「在台灣能夠成功的工作模式,是否能夠全然將其經驗移植到海外呢?」,那些台灣志工常自己認為的「好」,一旦不夠細膩或者缺乏與當地的溝通,就會變得荒誕無稽。
沒想到,脫離志工與學生身分後,前一陣子,這個教訓又繞回了我自己頭上。

可能我一股腦想改善貧苦與偏鄉辦學,看到太多學校經營辛苦,連小孩子的學習書本都買不起,有孩子看到我從台灣來,天真問我:「老師,您以前的課本也跟我們一樣嗎?」他手上拿著泛黃的複印課本,品質低落,打開內頁連個照片都是黑壓壓一片,根本看不清地圖上的黃河與長江在哪裡,我不捨地沉默以對。
這個不捨,便讓我起意動用身邊人脈,想從台灣找出版書商合作,聯合各種資源送到緬甸需要的地區,解決辦教育的燃眉之急。
卻沒想到,這件「好」事情從台灣起就被擋了很多次,我一直想用很有效率的方式,找到對口的政府單位,給我明確的答案與保證,讓我後續的業務能夠順利進行,結果只像個無頭蒼蠅到處尋不著標準答案,甚至不同角色間有衝突的答案。這時有前輩提醒我:「當妳把書克服萬難送過去,有人為你喝采,也有人的財路被妳而擋。」想的嚴重一點,可能進而威脅到我在海外工作的人身安全。
我回想起很多當地代表的保守回答,推敲自己的滿腔熱血下,必然排擠了既存印刷廠的利益,一陣沉默後,我笑自己有些傻,做決定的過程還不夠成熟。當然,這個故事的最後,我們單位還是把彩色課本送進了偏鄉,每年幾個貨櫃的庫存課本原本將被回收燒毀,藉此賦予它新的價值,重新跟當地對話、溝通,取得共識及平衡,改變的是,我不再講求對一個絕對性的答案,畢竟任何事情你在任何角度下,都只有看到部分,絕非全貌。
二○一九年,我找到了當初問我問題的孩子,我親手把彩色課本交給他,看他兩隻眼睛瞪得好大,直問我:「老師,這個是給我用的嗎?」我說:「是的,現在你的課本跟老師一樣,都是彩色的了。」
經驗是值得一提再提的,因為唯有不放棄的反省思考,柔軟的面對每一個不順利,減少甚至停止抱怨,放開你的包袱去接納「另一種文化思維」,才有可能在未來找出最佳解,否則,一味沉溺在計畫失落的情緒中,一直無法變通或轉彎,那麼國際志工之於你一點也不精采。
現在,我不敢說同樣的錯誤永遠不會再發生,但我很清楚知道:「多數時候,你看見的只是部分,更多赤裸的全貌,需要你放下國際志工的身分,去認識、去了解、去對話,甚至去感同身受,如此一來,你就不會覺得它荒謬至極,更不會認為這個世界都在跟你找碴。」
最後,想鼓勵每一位選擇踏上國際志工的人們,或者想了解海外非營利工作內容的您,就勇敢走出舒適圈吧!善用你的敏感來回應環境的變化,把握你的細膩來詮釋同理心,遇到任何問題,縱使它看起來這麼「不合常理」,也不要輕易下定論,不要嚼舌根到處八卦,或許你只是需要去車棚發呆,抑或找個前輩聊聊吧!誠心祝福,在反思過後,擁有一段很不一樣的國際志工旅程,也會對這些願意駐點在海外組織的工作人員,有更多的認識,因為這份志業要走得長久,不能只靠熱血、只靠愛,還要在每一次的「看見」及「相信」間,找到最微妙的平衡。

- 札記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