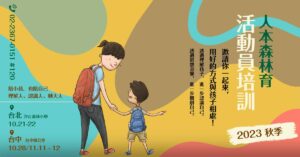面對壓力之下的不理性,可以怎麼辦?--也是超前佈署


莫名其妙的暴力,似乎越來越多了。大家都想問,萬一讓我遇到,我能怎麼辦?如果是那種「真正」的暴力,我想,誰也沒有答案:總不能叫大家去學武功吧?
不過,如果是遇到一些「不理性」的行為,例如,本來可以好好溝通,或擦身而過,卻突然暴發起來,甚至掄起拳頭,抓起重物…這個,我們倒是可以預做準備:就可能的發展、事情的本質,先在這兒想一想,談一談,應該是比臨時慌了手腳好吧?
我的意思,無非就是現在最夯的那句話:超前佈署!
既然說起時事,那就讓我跟大家講我的第一點。第一點是,如果一定要說疫情還有什麼好處的話,那就是:眼看對方就要giâ 起來了,我們可以在心裡告訴自己,這是疫情的作用。什麼意思呢?就是拿「疫情造成的壓力」做理由,為對方設想一個「合理的藉口」。(giâ,台語,類似「牙」音)
聽到「理由」或「藉口」,大家可能就要giâ 起來了:什麼?是他對我不仁,不是我對他不義,你竟然叫我幫他找藉口!然而,正是這一點,我想和大家深入討論。有一句話說:管控就像鍊子,當你把一頭栓在他身上的時候,另一頭也就栓在自己身上了。這意思是說,不讓對方自由的代價,總是失去自己的自由(因為你得時時看著他)。其實,怨怪亦然。怨怪別人的時候,我們便失去解決問題的機會了。
反過來說,如果能為對方提出一個解釋,我們便可以獲得冷靜思考、沉著應對的自由。
那麼,還有什麼比疫情更好的解釋呢?首先,它是一個無所不在的事實;其次,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受到它的影響,心情受到左右,思緒受到干擾;最後,它最「無辜」,也就是,最不會牽拖到其它人或事。至於它是真的理由,還是鬼扯的藉口,一點關係都沒有;因為,我們、而不是對方、需要一個解釋,讓自己穩住。
以上的論述,有很多人不能接受。這也是我很想和大家討論的:我們常常不自覺的「需要」指責別人。如果自己也有些責任,這當然是卸責之必要;如果自己毫無責任,「怨怪」也可以讓自己偷懶,不去思考怎麼解除危機,這就覺得輕鬆;直到危機傷害到自己,還可以用受害者的身份,更進一步地怨怪、指責對方。這種心理機轉,是人放棄主體性的重要表徵。
從這個角度去看,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麼無論哪一個社會,總是有一定比例的人不肯理解加害者;拒絕理解、專心指責,可以免掉做為公民社會的一份子、 理當承擔的改進社會的公民責任:只要把加害者「解決」掉,就心安了;完全忘了那句老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加害者總是絡繹不絕、「解決」不完的,如果我們不去解決產生加害者的那些根本問題的話。
話題說遠了,讓我們回到現在的主題。如果大家願意把對方的行為解釋為「壓力下的反應」--壓力是否真的來自疫情也不是重點,我就可以來談第二點。第二點是,告訴自己:他不是「有意」衝著我來的,即使看起來是針對我,但也是在壓力下的身不由己。這麼一來,就可以讓自己脫身,把自己排開,從第三者好像事不關己的角度,來檢視當下的情況。這麼一來,就完全避免了刺激對方的任何可能性,因為,反正他惹的那個人又「不是」我,而他也「不是」本來的他,那又何必反惹回去呢?
這樣,雖然未必能讓對方冷靜下來,但至少不至於火上加油;但更重要的是,我們便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內進行客觀的分析:這個人的「罩門」在哪裡?怎麼做才對他有效?
如果是父母,他多半是出自對我的關心,以及「沒關心到」的不滿和焦慮;例如,看到我又沒戴口罩就想出門,多次警告無效之後,就抓狂了。這時候,最明智的做法,不就是趕快把口罩戴上,甚至不必多說一句話?不要以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如果不能理解對方,不能依循前述的兩點讓自己從「現場」抽身(在心理上)的話,很可能就是:當場把口罩丟到地上,用力踩幾腳,再大聲喊道:都是你這該死的東西!這樣的話,接下來的後果就只有四個字:不堪設想!
如果對方是「在家上班」的家人,擔憂變成「在家又不用上班」也許就是事情的源頭;這時候,先不用管他口中罵些什麼,手中拿著什麼,地上已經摔碎了什麼,也許應該跟他說:我知道你很想去辦公室…當然啦,這個說法搞不好會變成提油救火,這得看他的個性,處境,以及平時相處的模式如何;不過要能即時做出評估,首要條件還是前述的兩點,讓自己成為解決問題的人,而不要變成被解決的問題。
如果對方是個「路人甲」,正在揮著手中的「武器」(希望只是一把傘),這時候,即時想起「疫情」兩字是合宜的;因為,「無差別暴力」正需要「無差別解釋」。解釋有助於化解恐懼,消除恐懼有助於找到「盾牌」(背包、纏在手臂上的外套,或雨傘?),並「規劃」逃走的路線。
接著前面的「例如」和「如果」,就來跟大家講我的第三點。第三點最重要,就是,「思想演練」。科學研究有一個重要的方法,叫做「思想實驗」;意思是,不必真的動手,只要在頭腦中設想各種情境和條件,再運用已有的知識或理論,去推測可能的結果。借助「思想實驗」這個名詞,我所謂的「思想演練」就不是演練思想,而是透過「思想」在頭腦、而不是實境、中,模擬可能的事件,設定可能的角色,用想像的方式,演練自己可以選擇的最佳反應模式。
要進行這第三點,最好要有個同伴;沒聽過「孤掌難鳴」嗎?一個鑔鈸不響,總要兩個人才能演練。就伴侶而言,這個演練可以增進兩人的感情,加深相互的感應,不用說,更可以減少相處時難以避免的磨擦,降低兩人中的任一人成為「不理性對象」的可能,說起來,就是「一人吃,兩人補」--雖然是由閱讀此文的一人發起,但演練的收獲卻是二人共享,世上再也沒有比這個更划算的事了。
如果是親子或師生一起「思想演練」,那就不止是划算,更是教育上的重大成就了。年輕人素來的感受,師長們無非就是發號施令者;做人該當如何,題目怎樣解答,無非就是他們說了算。現在,有大人和他站在同一高度,共同探索誰也難以預料的未知情境、那人會做什麼、我可以做什麼…最重要的是,這個探索的過程,是雙方各演一個角色;但不是照著既定的劇本,而是一面演,一面商量劇本怎樣才合理,而且,這合理與否的判斷,是在雙方「思想」的交織之中進行的…
最有意義的是,演過一套之後,角色可以交換;這時候,小孩就充分地體會了:他可以做我,我也可以做他:隔閡消除了,思想提升了,知識增長了,見識開展了,因為,在這過程裡,大人不必擺出指導者的面孔,但仍然提供了很多小孩原先想都不曾想過的事情。
不過,無論是哪一種「演練」,一定不要忘記時時回到前述的第一和第二觀點;否則,容易陷在動作和台詞之中,那不但有點可笑,只怕會帶來更多的挫敗感。
說是疫情之外還有另一種疫情,說是壓力之下難免引發暴力,好吧,這也是沒辦法的事;不過,不管怎樣,超前佈署總是沒錯的啦!本文出自人本教育札記372期


2023工作報告_玩的教育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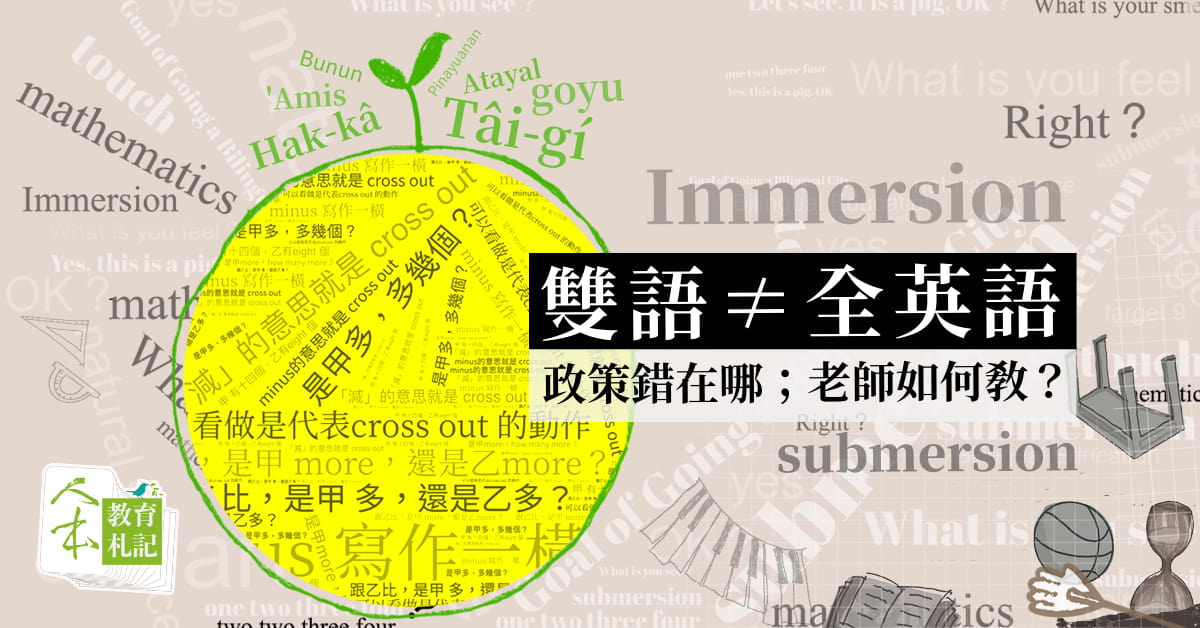
【專題】雙語 ≠ 全英語!──政策錯在哪;老師如何教?

GiveMe5 我不打小孩 家庭動起來記者會

打造愛的家,我不打小孩。台灣兒權向前行!我們可以!

快樂父母班

你們挺暴力,誰來挺小孩?!校方縣府聯手放水,我們要求依法處理
本會接獲家長投訴,去年(2024年)2月他們向雲林縣西螺國中申訴廖姓專任教師與蔡姓兼任教練嚴重體罰與霸凌羽球隊學生,校方和縣府疑似輕放處理……

客家電視台送學生入狼口?!文化部應建立機制,勿使藝術文化成為性平死角
2023年6月,李菄峻(原名李文勳)性侵學生案曝光;2024年3月遭戲曲學院終身解聘。然而,他竟仍參與客家電視台節目編排,甚至讓戲曲學院學生在不知情下前往其住處排練……

需要徹底的轉型正義,才能阻擋戲曲學院的悲劇
戲曲學院多起身心暴力,性暴力的案件,尤其是李菄峻歷年多次性侵學生案,經監察院調查屬實,並提出糾正。本會認為,本案的處理,需要校園轉型正義……

體育暴力層出不窮,運動部能為孩子把關嗎?
體育和運動訓練中的暴力不但頻繁發生,且相比其他教師不當管教行為,往往更加嚴重。學校的漠視、主管機關的不重視,形成一種學生運動員在受不到保護的情形下進而認同、甚至複製暴力,使得傷害一再持續發生的循環……

學校連三罪行:吃案、沒收不適任、強逼轉學!市府缺席!人民無奈?
本會接獲家長檢舉臺中市大安區國小王姓總務主任霸凌學生、將學生鎖在儲藏室內、逼迫學生轉學,家長向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均遭敷衍回應,容許學校拖延長達兩個月才啟動調查。今調查結果出爐,調查報告竟認定王姓總務主任的行為不成立霸凌……

面對困難 學輔效能才有機會進一步提升
台灣近年學生自殺、自傷人數不斷攀升,在上一次兒童權利公約國際審查時,來台的國際專家特別指出「自殺率上升並非歸因於兒少個人議題,而是導致心理不健康更廣泛的結構性議題,包括學業壓力、霸凌及不當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