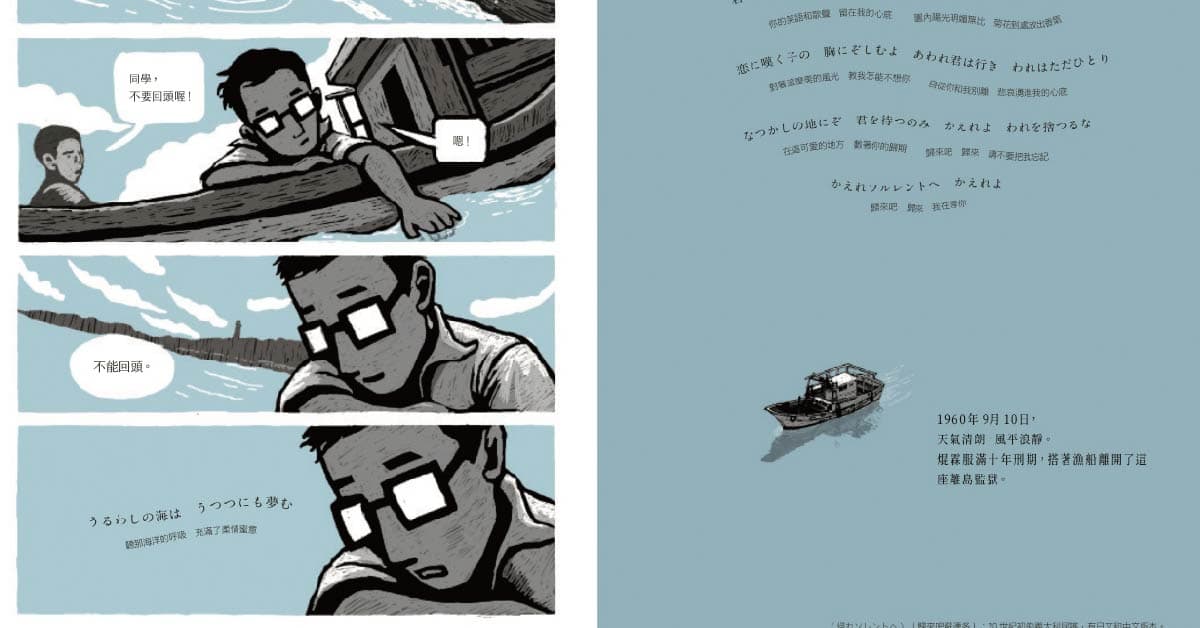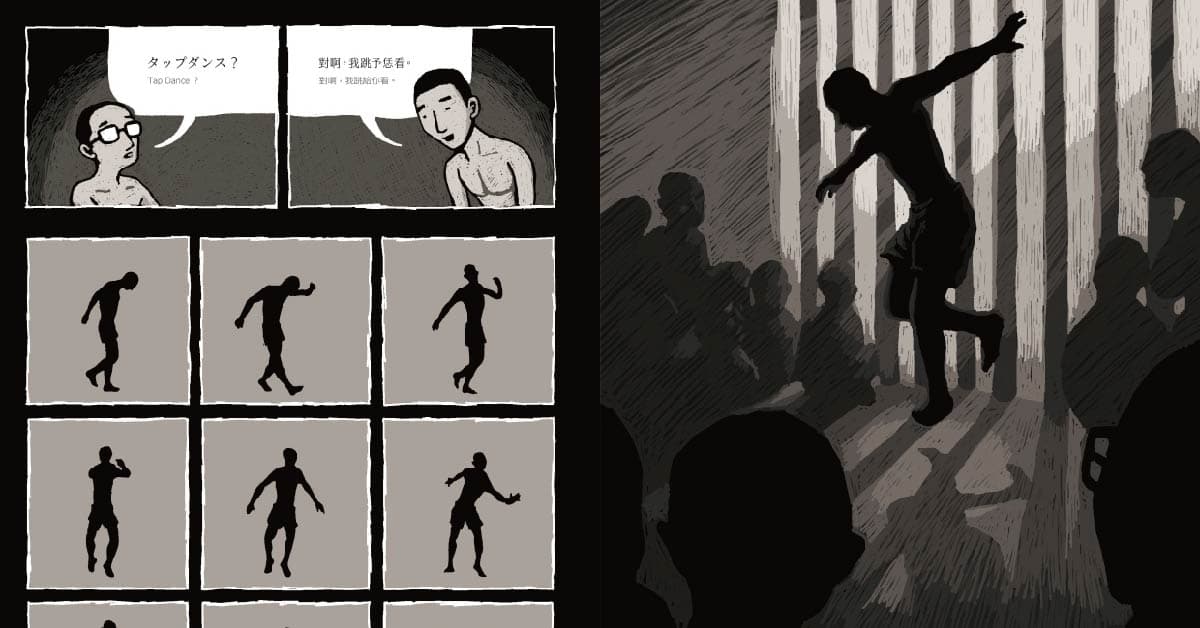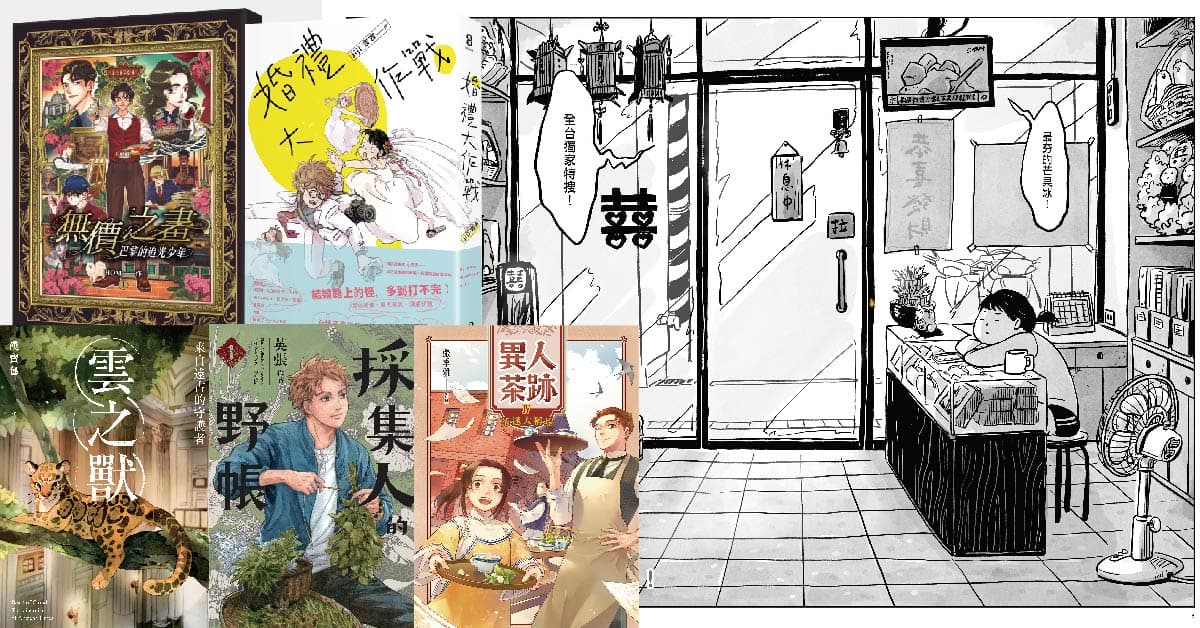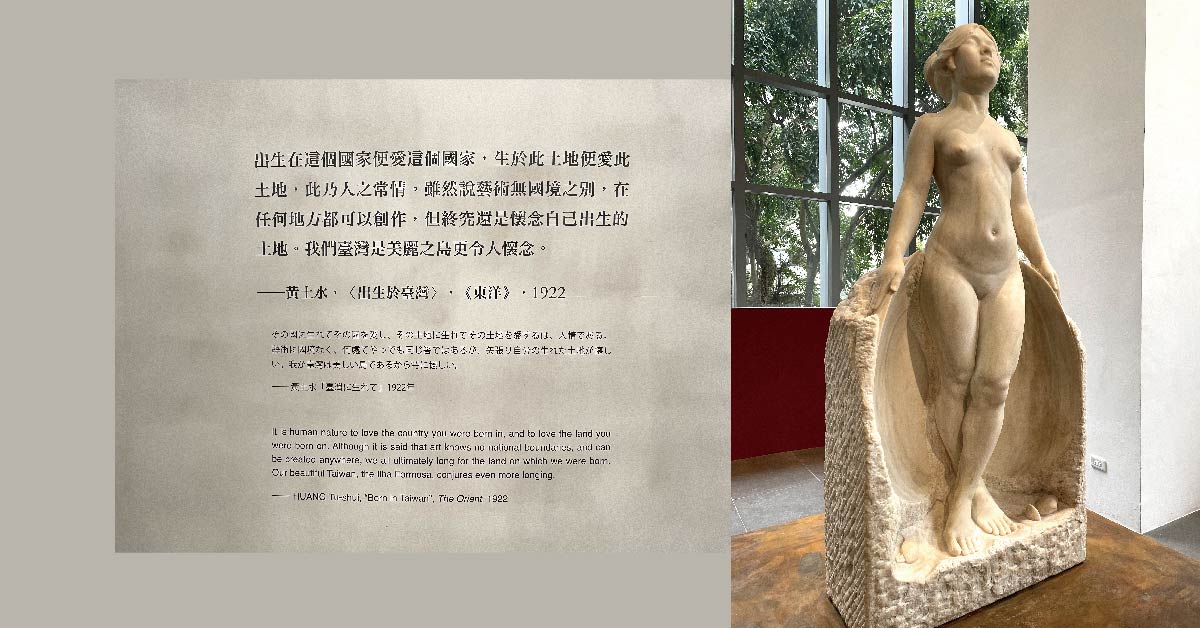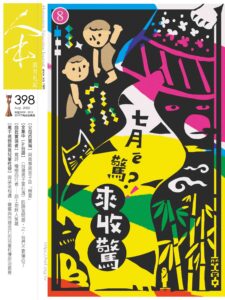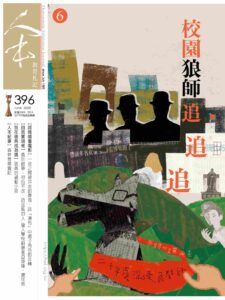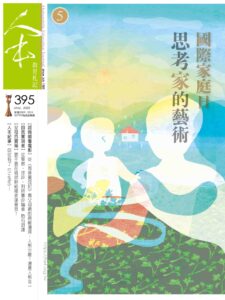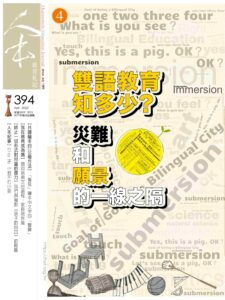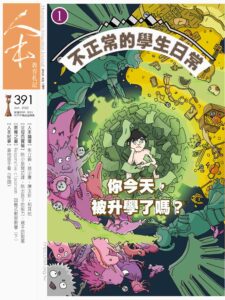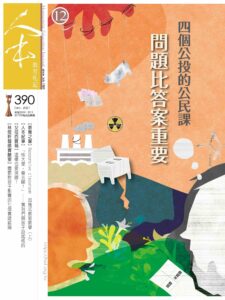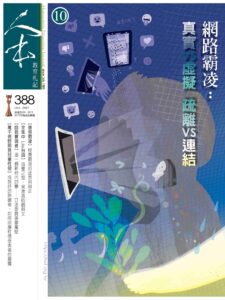從基地到社會─基地論壇談死刑 | 人本教育札記

死刑,對我們這些「平凡且守法的公民」而言,是個極其遙遠且模糊的議題,頂多就是在看到某些社會新聞時偶爾想到的一個「概念」,更遑論三重青少年基地這群十多歲的國、高中生了。
基地的青少年們,多來自資源不多的家庭,單親、隔代教養、新住民等背景的孩子不在少數,甚至有孩子的家人就是服刑中的受刑人。大家背景不盡相同,但共同之處就是,這些來自家庭、學校與環境的困難,經年累月的,都成了基地孩子發展的阻礙。
對這些孩子而言,生活(甚至生存)的擔憂就已經夠多了,為什麼我們非得在基地唯一的必修課──論壇──中,和他們討論「死刑」這種抽象又看似遙遠的題目呢?而我們又能如何與小孩一起思考,死刑存廢和社會中「每一個人」的關係?
剛聽到主題是「死刑」時,小孩的反應清一色都是「這關我什麼事啊?」、「我又不可能去殺人,知道這個要幹麻?」。確實,每每遇到這種社會議題時,該如何讓小孩「有感」,是基地備課時最大的困難。於是,這學期基地大人和廢死聯盟的同仁們,共同精心設計了一系列的論壇教案,前後總共花了四次論壇(八小時)的時間,帶領青少年一起靠近這個話題。
我們先看了韓國電影《菜鳥陪審團》,花一點時間討論臺灣未來的「國民法官」政策,讓孩子想像若自己是陪審團一員,審判中什麼事情會最重要。接著,我們讓孩子回想自己「犯錯的經驗」,並用化名寫下當時的過程,以及當時希望其他人如何對待自己。這些討論,都在試圖讓孩子對「司法審判」中不同角色的歷程有感──一旦孩子發現「犯錯」或「判決」都可能與我們每一個人息息相關,才正式談論臺灣遭判死刑的幾個案例。

從近期的王信福,到過往的幾個案例,如鄧如雯、湯英伸等,至最後一堂課中,廢死聯盟夥伴提的鄭文通,我們不斷換著方式,一會兒要孩子扮演案中不同的角色,模擬「一般民眾、法官、被告本人、受害者家屬」等不同角色;一會兒透過「象限遊戲」,從「不同情與同情」、「判死刑與不判死刑」區分成的四個象限中,隨著案件越來越多細節被揭露,要孩子調整(或不調整)自己的立場;一會兒又遮住案件脈絡,只以「加害人背景、犯案手法、和解與否」等條件製成表格,要孩子猜測這些案件最終的判決結果。以上這些練習,都是為了讓小孩更深刻感受到「死刑」作為刑罰最高手段的意涵、裁決時的困難、它的不公平與不可回復性。
但這些活動的過程中,最令我感到驚豔的是小孩不斷提出的困惑及看法:
「如果湯英伸活在現代,是不是就可以去告雇主違法?」
「為什麼鄧如雯不逃走就好?」
「這些線索不夠,一定有詐,我先不要下判斷好了。」
「為什麼王水殺人的才判十八年,而誤殺人的人會被判死?」
「為什麼政府(事實上是司法體制)就可以殺人?」
「如果死刑執行時,死刑犯進行抵抗,算是『正當防衛』嗎?」
產生這些疑惑簡直太好了!有問題,才有可能做更深的思考。況且這些思考,正是我們平常身為一個新聞閱聽人,在這個只求速度、求激起群眾情緒的網路世代裡,非常難能可貴的。基地的論壇中,有機會讓孩子「主動」對犯罪事件、刑事審判、甚至是對剝奪生命權作為處罰手段感受到困惑,並且發自內心地想得到解答,而非在大眾輿論中一味跟風,我由衷認為,這就不枉費我們絞盡腦汁準備的教案了。
在這系列課程中,我們另外還對於不同類型的人權、法律與刑罰的目的、乃至於「支持與反對死刑的人」各自有怎樣的理由…等等,進行許多討論和猜想。儘管帶討論的基地同仁及廢死聯盟的夥伴們,都已有自己對死刑存廢的立場,然而,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有表態,更沒有要求小孩選邊站,而是不斷用問題引導他們,以更宏觀的視角來討論、追問。
在「連結其主觀經驗」與「指引其客觀思辨」之間來回切換,很燒腦,卻也果真愈來愈靠近議題的核心──人權與法律之間的關係,以及更重要的是,社會案件中的完整脈絡,與其中結構性的問題。
最後,我非常喜歡廢死聯盟的副執行長為這系列課程紀錄所寫下的結語,請容我在此引述:
「三重青少年基地想透過議題的討論,帶領基地的孩子從整體社會脈絡去思考,看見自己的處境,也看到這些身邊的議題和不同處境的人,在孩子心中種下一顆芽、一株根,等待他們發芽茁壯的時刻到來,他們才能穩穩地知道自己站在哪裡,不至於感覺孤單無援,能夠找到自己面對困境和挑戰的力量。」
如何給孩子更好的教育?為人父母/教師的您,是否正在追尋答案?進步的源頭,來自不斷的思索與釐清。《人本教育札記》多次榮獲金鼎獎、金蝶獎的肯定!國內第一本為家長及關心教育者所編寫的專業教育月刊,提供您看教育的不同角度。每個月都陪您,一步一步向前,充實自己。
- 本期特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