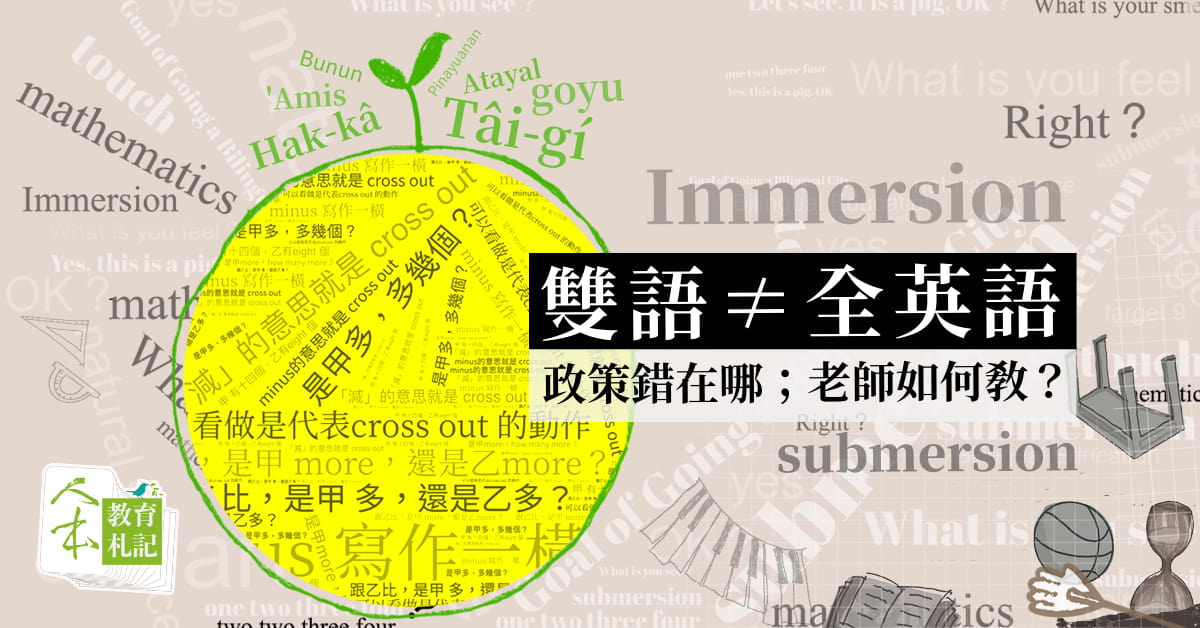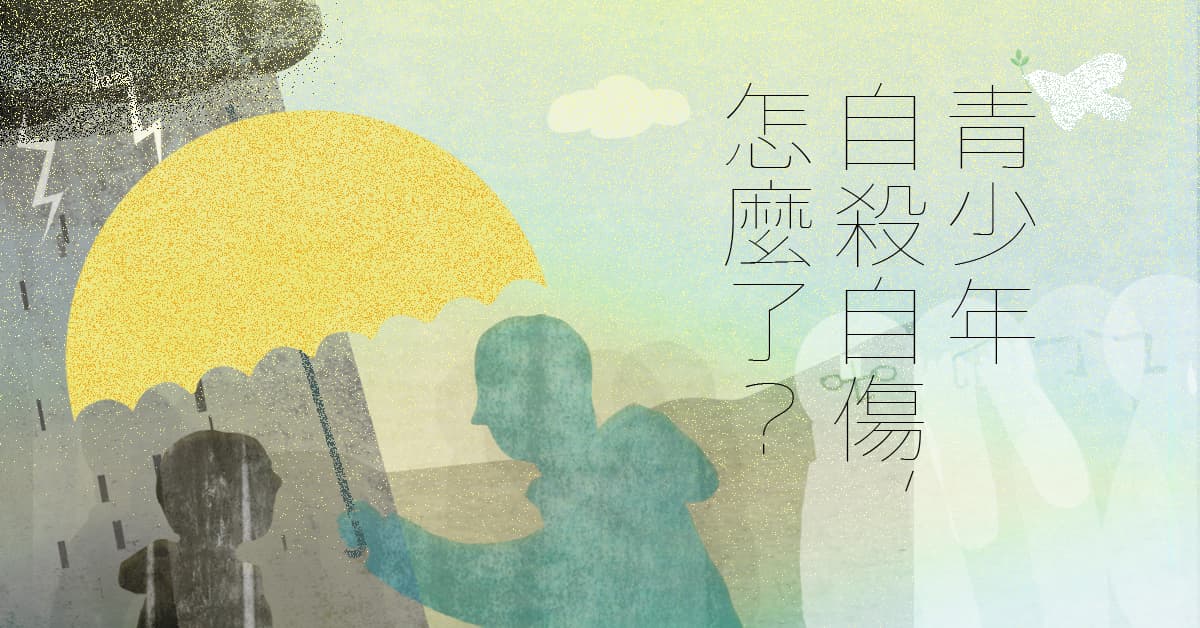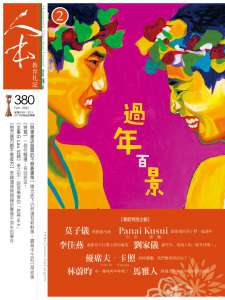先有邦交才有幫助?

--本文刊登於人本教育札記384期
在小規模的非營利組織工作,有很多事必須自已來,不只是非洲端的工作執行,連臉書粉絲專頁的留言回覆,都得親上火線;在粉絲專頁上提問的人雖然多,但問題皆大同小異,如果要問我,什麼問題最難回答?我想應該是「肯亞跟台灣沒有邦交,為什麼要援助他們?不應該先從有邦交的國家進行援助嗎?」
第一次去肯亞之前,協會同仁提醒許多在機場必須注意的事項,加上中國一帶一路的政策,國籍所帶來的問題使得我們得特別小心。抵達肯亞當天,飛往奈落比國際機場的班機沒有坐滿,除了我們之外還有一些零星的中國人,其它大多為返回本國的乘客。下飛機前有幾位當地人非常熱情地向我們打招呼「My friend! welcome to Kenya」,面對這樣的友善歡迎我心想:「其實肯亞人還蠻友善的嘛,看來是太擔心了。」。
然而,在入境的那一刻起,剛才的好心情立即煙消雲散;肯亞政府不承認中華民國護照,海關不會直接在護照上蓋章核準入關,除了事先在線上辦理肯亞簽證之外,到了當地還需要由海關人員現場審核,向主管提出入境許可申請,辦理人員將核淮單釘在護照上才算過關;很多海關人員覺得麻煩,看到我國護照都不想辦理。
看著自己的護照被丟來丟去,拿進拿出時,才發現剛才在機上的我實在是太天真。經過一個半小時,好不容易辦好入關終於可以領行李了,卻又在領完行李後,被攔截要求開箱檢查;檢查的同時,海關不斷跳針地問我們「你們為什麼要來?」(我們在肯亞是合法的組織,來幫助你們政府沒有能力照顧的人民) 「行李裡為什麼有蠟筆?」(蠟筆是要帶去孤兒院給孩子的)「裝蠟筆的盒子裡為什麼有塑膠製的夾層?」(肯亞有嚴格的塑膠禁令,但是是針對塑膠袋,不是這類物品),再多的解釋跟說明,都無法離開,只因為我們不肯給對方五十元美金的「罰款」,直到我們聯絡上當地有力的地方人士,才得以走出機場。
2018年布吉納法索與我國斷交後,史瓦帝尼成為目前台灣在非洲碩果僅存的友邦,我國政府每年在各方面投入許多的協助,維持這個長達53年的友誼;當然史瓦帝尼國王也以友好相待,成為中華民國的友邦元首中,來往最為頻繁的一位,即便中國履次釋出善意嘗試建交,仍改變不了史國與我國間深厚的情誼,甚至願意在國際場合上公開力挺台灣。
與史瓦帝尼這個情義相挺的友人相較,更加突顯出我們對其他國家的一廂情願,即便協會已是肯亞在地的CBO(community based organization社區組織),但少了友邦關係,還是會面臨在肯亞機場這樣的窘境,說穿了就是「我幫你,但你不一定會幫我」。照這樣的邏輯來看,台灣人起家的跨國非營利組織,是否更該把援助的資源投入在那些友邦之中?那個我認為最難回答的問題,看起來似乎有正確答案。
我們長期投入援助工作,看到非洲許多國家因著內戰、政府資源分配不均、甚至受到全球氣侯變遷造成水旱災的影響,在社會底層求生的人民,長期處於赤貧線下(聯合國的量化定義為一天生活費不到1.25美元,即是赤貧狀態),這些世界難民不單在我們的友邦之中,而是在各國、各地。
2021年世界銀行統計,在新冠疫情影響之下,極端貧困總人口數,從原本的7.03億人,將增加至8.79億人,他們與那些在機場裡依循國家政令辦事的人員們有著截然不同的生活;有些人終生沒有領過身份證,更別說是護照,現今的總統叫什麼名字,可能也不是很清楚;沒機會受教育的他們無法閱讀,資訊的取得永遠晚一步;如何填飽肚子、讓自身可以維持「生存」是他們每日最掛心的事;有一半的孩童因缺乏乾淨的水資源飽受痢疾所苦,甚至失去生命,更有許多貧困家庭無法負擔一雙鞋子,孩子的雙腳被沙蚤咬得慘不忍睹卻也不知該找誰求助;當這些脆弱的生命就在你面前時,確實難以將「有邦交」做為援助的先決條件。
去年一整年全球遭遇疫情肆虐,非洲各國政府在防疫上做了嚴格的封城措施,不但強硬禁止人民外出群聚、停止商業行為、也同步實行宵禁管制,街上更有荷槍實彈的軍人監控人民的行蹤;看似得以有效防止疫情擴散,然而有一半以上居住在偏鄉的居民,受到外出限制而瞬間喪失謀生的能力,對於積蓄短缺的「赤貧」居民,封城也等於斷絕日常維生的糧食。當每天生活費不到1.9美元,到底要先買什麼來囤放以面對未知疫情,成了最難的選擇題。
悉知這樣狀況的我們,立刻決定在台灣發起募資,為烏干達貧民區以及肯亞偏鄉部落發放糧食急難救助包,內有白米、大豆、玉米、小米、鹽、糖、茶葉、油、肥皂…等民生用品。雖然我們沒有能力阻止疫情,但我們可以讓飢餓暫時停止;同時搭配已經在當地運作多年的活水(水井開鑿)與興學(興建教室)這兩個子計畫,在學校與村落中設立洗手站,倡導洗手的習慣,加強防疫與個人清潔的衛教。
看著一袋袋食物被發到有需要的居民家中,孩子們也開始主動去洗手站洗手,不禁聯想到過去1950、1960年代的台灣,也曾接受過其他國家非政府組織的援助,甚至更早期的馬偕、馬雅各、孫理蓮等人,在台灣行醫、建醫院、學校,推動教育,扶持弱勢得以自立,這些人也並非全然都是因著友邦國籍的關係才選擇前來幫助。因著這段過去,台灣走過政治、經濟的穩定發展及教育普及化,如今我們也有能力成為幫助發展中國家進步的朋友。
公益平臺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嚴長壽先生,近期因新書受到天下雜誌的採訪,訪談中嚴董事長說到,就多年的經驗來看,台灣一直以來都不是全球遊客的旅遊首選,既然如此該如何發揮自身的優勢?他以台灣人對中國汶川地震與日本311地震的援助為例:
「幫助別人絕不能是,你跟我有邦交,我才幫助你,這不是我認為的文明。文明是周圍所有的鄰居,不管喜不喜歡,只要我能夠幫助你,你不提我的名字都沒關係——這才是真正讓人打從心裡能接受,並非有條件、有代價或給壓力。」(註)
嚴董事長雖然從觀光產業的角度切入,但這樣的觀點與視野,足以解答那個最難回答的問題。至於我,倘若能以台灣之名在世界各地注入一些改變,那怕沒有邦交,但願能與芥菜種會創辦人孫理蓮女士的心志一樣「哪裡有需要,就往哪裡去。」
註:出自天下雜誌《業者狂做「偽出國」 嚴長壽:只會加速毀滅台灣》
圖、文︱MONICA(舊鞋救命營運總監)
- 精選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