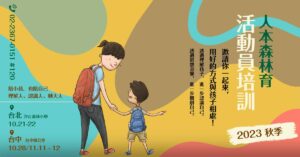性侵加害者利用什麼來達成目的?──談兒童的「脆弱因素」


澳洲一名下半身癱瘓的女孩Audra,十二歲時母親去世,父親取得她的監護權。她大多生活與學習的時間,都在特教學校中度過。在她就讀的第一所特教學校,她被較年長的同學持續性侵。Audra十多歲時,學校的維修人員會故意損壞她的輪椅,例如刺穿輪胎,使她每天都要去找他。維修人員會綑綁她的雙手,使她無法逃脫,並性侵她。侵害的行為維持了六個月,嚴重時一天更侵害達三次。維修人員威脅Audra,若說出去,會殺死她和她的家人。當時Audra感到十分無助,沒有人可以幫助她。(註一)
所有兒童都面對著性侵的風險。在特定的危機因素下,兒童會變得更為脆弱。Audra的經歷中,母親早年離世,使她缺乏母親的保護。她行動不便,需要他人照顧。在特教學校中曾被同學性侵的經歷,讓她在喪母的創傷下再次受創。機構式的照顧環境,令她不容易與其他成人聯繫。一連串的因素,讓Audra暴露在脆弱的處境中。
澳洲皇家調查委員會(The 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在2017年發表全國機構兒童性侵調查報告,針對在學校、家外安置機構、宗教團體、體育訓練中心、青年感化院等機構發生的兒童性侵進行全國調查。經歷五年調查、57場公聽會、8013場保密面談後,共有6875位倖存者敘述了受害經歷。澳洲皇家調查委員會根據上述資料,整理出兒童面臨性侵危機的脆弱因素(vulnerability):
- 兒童的性別
- 兒童的年齡及發展階段
- 兒童先前的受虐經歷
- 兒童是否有身心障礙、身心障礙的類型
- 兒童的家庭處境
- 兒童對性行為、性侵和人身安全等議題的理解程度
- 機構的活動性質、兒童的參與程度
- 其他因素:高成就的兒童、性取向、性別認同
擁有上述脆弱因素的兒童,不等於就會經歷性侵。沒有上述危機特徵的兒童,也不等於不會遇到性侵。然而,辨認兒童性侵的脆弱因素會幫助我們提高敏感度,更早的察覺潛在受害者。
以下,我試著分項整理兒童受性侵的脆弱因素;從理解這些因素開始,可以思考現在兒童保護網的漏洞,促使我們更積極的推行預防措施。
性別
澳洲皇家調查報告指出,大部份關注兒童性侵的研究均顯示,兒童性侵受害者多為女性。然而現有的研究發現,尚不能對兒童性侵的性別模式,提供清晰的答案。社會中主流文化的性別刻板印象、性別不平等及性化女性的現象,能解釋為何較多女孩遭受男性加害者性侵的部份原因。
雖然研究指出兒童性侵受害者以女性佔較大比例,但出席澳洲皇家調查的性侵受害者中,男性卻比女性受害者為多,佔64.3%。而在宗教組織管理的兒童機構中,男性受害者更高達70.1%。這數據有幾個重要的意涵。
首先,兒童的性別在不同年代及不同類型的機構中,呈現不一樣的風險。
在1950至1990年代的兒童家外安置機構及寄宿學校中,男孩似乎更容易遭受到性侵害。2000年代至今,在托兒所、體育訓練中心、近代社福機構營運的育幼院及寄養機構等場域中,遭遇性侵的女生比例則較高。
我們必須注意兒童性侵的通報率,往往低於實際發生的個案數字,所以上述的數據沒法完全反映男孩和女孩遇到的性侵狀況。儘管不論性別的性侵通報率均偏低,男孩性侵的通報率卻可能更低。例如在體育活動中,性別刻板印象和對男性陽剛氣質的期待,使男孩經歷性侵後,不傾向通報。所以我們需要注意不論性別的兒童,都同樣面對兒童性侵的風險。

年齡及發展階段
兒童的年齡和發展階段,是另一個影響兒童遭受性侵害的風險因素。年齡會影響兒童接受照顧的依賴程度、求學而身處的機構類型、情感及情慾發展。
根據澳洲皇家調查報告,6875位出席保密面談的倖存者中,0-4歲的受害者佔5.95%,5-9歲的受害者佔31.1%,10-14歲的受害者佔51.5%,15-17歲的受害者佔11.5%。
五歲以下的兒童主要在家裡接受照顧,降低了他們在機構環境中遭受兒童性侵的風險。基於這些兒童需要較多的關注及緊密的照料,所以在托兒所等育兒機構中,通常有多於一位成人在公開的環境照顧嬰幼兒。成人不易與幼兒有獨處的機會,某程度降低了嬰幼兒在機構環境被性侵的危機。然而嬰幼兒在機構中遇到性侵的案件數字偏低,也有可能因為年幼孩子對理解、描述、回憶或揭露性侵的能力有限。故年幼兒童的受害狀況較難反映在通報數據中。
在澳洲皇家調查報告中,最高比例的受害者在10-14歲時首次遭到性侵害。兒童在這發展階段,學校生活、課後活動或休閒活動漸多。他們越來越獨立,在生活各層面擁有更多自主權。同儕關係也變得更有影響力。青春期伴隨的情緒和身體變化,他們會對戀愛、性、親密關係感到興趣,也會探索自己的性取向和性別身份認同。性侵加害者可能會利用青少年這些發展與變化,進行性誘騙。加害者也可能利用青少年對關係及性的好奇與知識不足,誘騙他們進入性化的互動。
15-17歲的青少年,比起兒童更獨立,更常有機會與成人獨處與自由行動。雖然這年齡層的受害比例相對10-14歲青少年為低,但澳洲的皇家調查報告指出,這年齡層的青少年若缺乏對積極同意權、互相尊重的親密關係等概念,較容易被有照顧或教育責任的成人(例如體育教練、教師等)利用。青少年在發生性侵後,也不傾向通報。
先前的受虐經歷
很多兒童及青少年在遭受性侵前,曾經歷不同形式的不適當對待,例如性侵、身體暴力、情緒虐待、疏忽照顧及遺棄。創傷的經歷,使兒童更為脆弱,增加了兒童遭受性侵的風險。
虐待及性侵的遭遇,與兒童之後再次受害(re-victimisation)有顯著關聯(註二)。澳洲一份關注兒童性侵受害者的研究發現,183位兒童受害者中,十分之一在早前曾有受性侵經歷。研究者在六年後追蹤這些兒童的狀況,高達六分之一的兒童再次經歷性侵害。(註三)
虐待的經歷對兒童的情感、認知、心理、人際關係、自我形象等發展,帶來嚴重和長遠的影響,使兒童變得非常脆弱,容易再次受創。虐待所帶來的影響包括:
- 自卑、低自尊心、羞恥、習得的無力感、混亂的認知;
- 與同儕難以建立良好關係,容易被同儕排斥,感到被社會隔離;
- 情感不安,需要情感關注;
- 與家人或照顧者的關係不好;
- 虐待直接導致兒童的發展性障礙(developmental disorders)或認知障礙(cognitive impairments)。
澳洲皇家調查委員會發現很多受害者在家外安置期間,遇到性侵。曾經歷虐待的兒童,在育幼院、少年監護所、寄宿學校等機構的照顧與學習環境中,會更為脆弱。這些兒童大多是因為在家裡遭受不適當對待,才被安排家外安置。但他們在安置機構卻沒有得到基本的保護,反而經歷更多的傷害。
由於機構的環境與活動的性質,提供了成人與孩子獨處的機會。加害者也有機會利用受創兒童期待情感關注的復原需求,與孩子發展緊密的情感關係,取得信任,進而展開對兒童的性誘騙。另外,由於機構的照顧環境,不見得時時刻刻會有成人監督,兒童在機構中也可能面對同儕的霸凌或不健康的性互動。
因為國家戰爭、饑荒、政治迫害等因素而逃離家園的難民兒童,他們在自己國家已經歷不同程度的迫害,再加上逃亡期間的流離不安,累積的創傷使難民兒童在其他國家尋求庇護時,需要更多的保護與復原支持。然而,在難民營中,難民兒童因為社會隔離、情緒困擾、語言不通、對未來的不安,使他們變得非常脆弱,容易成為性侵加害者的目標。
身心障礙兒童
身心障礙兒童比其他兒童更容易受到性侵害及其他形式的不適當對待。美國一份研究發現,身心障礙兒童比一般兒童遇到性侵的比例高達3.14倍。(註四)澳洲皇家調查報告更指出,身心障礙兒童受到專業人士性侵的風險更高。
不同的身心障礙類型帶來不一樣程度的風險。智能障礙、溝通障礙及肢體障礙的兒童,遭受不適當對待的風險特別高。
溝通障礙的孩子礙於較難表達性侵的經歷、無法像其他人那樣輕鬆地溝通、提出申訴、命名加害人的名字,使他們容易成為加害者的目標。
智能障礙或認知障礙的兒童,則常被認為缺乏能力,而不被相信,甚至認為他們是不可信的證人。加害者故意挑選他們認為「能力較弱」的孩子,或不被成人相信的兒童,作為性侵的目標。
肢體障礙的兒童因行動不便,在個人衛生及醫療方面較大程度需要依賴他人照顧,因而容易成為性侵加害者的目標。肢體障礙的兒童大多長期接受成人的親密照顧,包括洗澡、換衣服、睡覺等。肢體殘障的兒童對自己身體的完整性及自主權,因而受到干擾,讓他們感到自己的身體不屬於自己的私人領域。(註五)若缺乏尊重兒童的照護以及適當的教導,孩子對什麼是適當的身體接觸、哪些是安全的互動,會難有清晰的理解。
而在「封閉式」的機構照護環境(”closed” institutional contexts),例如特教學校、寄宿學校、喘息照護中心等,身心障礙兒童遇到性侵的風險更高。這些機構式的照顧中心或學校,通常有非常嚴格的生活及活動安排。孩子對生活的安排甚少有控制或選擇權。同時,在照護機構中不論是日常生活、教育、醫療、溝通、交通接送等層面,常有多位成人,甚至陌生人參與其中,讓兒童難以快速判斷誰可信任。
照護機構中牽涉身體親密接觸的照顧,也主要在隱密的空間進行。若發生性侵時,不容易被第三者發現。有些加害者濫用職權賦予他的照顧責任,把性侵包裝在一般的照護行為下。例如在協助兒童洗澡時,不適當的撫摸兒童的身體、清洗的時間過久、花很多時間幫孩子擦乾身體,使受害兒童難以及早察覺及辨別。而身心障礙兒童集中照顧的環境,可能只有一兩位成人在場,使同儕之間的霸凌及不適當的性行為,也難以被發現。

兒童的家庭處境
兒童在成長的歷程中,很多面向皆需要依賴成人的照顧與保護。他們的體型、力氣不但比成年人弱,也相對缺乏社會制度和法律層面的權力。兒童依賴父母或照顧者提供安全穩定的生活環境與情感連結,才能健康成長。
兒童的家庭若充滿衝突,家人之間互相暴力對待或關係破裂,將會減少兒童得到的照顧與關注。有些兒童甚至受到家人的虐待、性侵。在缺乏家人的保護之下,當兒童在學校或其他場域中感到不安全或遭受性侵時,他們會感到沒有人會幫助他們。
兒童性侵加害者會傾向挑選缺乏家庭支持的孩子作為目標。家人無法照顧孩子的原因很多,包括父或母過世、離婚、酗酒、藥物濫用、精神疾病、生病、入獄等。家庭成員例如手足的生病或過世,也可能會讓父母過於哀傷,而沒有多餘的力氣去關注家裡其他成員。貧窮的困境,可能讓父母忙於養家餬口,以致沒有時間注意家裡孩子的狀況。受害小孩可能感到父母已經承受很大壓力,不想因為自己的遭遇增添父母的困擾,而選擇不對外揭露性侵。
在育幼院、寄養家庭、寄宿學校、少年監護所、難民營生活的兒童,他們沒有跟父母同住,身邊缺乏保護他們的成人,而容易成為加害者的目標。這種與社會隔離的機構環境,兒童不容易取得對外的聯繫,他們的處境會變得相對脆弱。
高成就的兒童
社會往往期待兒童要「勇敢」說出性侵的經歷,但從來沒有思考過兒童揭露性侵後可能面對的困境。其中,有些受害兒童因為擔憂揭露性侵,會影響他們的發展或求學的機會,因而延宕揭露的時機。
例如國家體操隊的選手,可能非常依賴特定的教練與醫生,或是依賴某機構安排的培訓與參賽機會。受害兒童會恐懼性侵的揭露,會危及非常難得的海外培訓或參賽機會。若加害者是該領域德高望重的人,受害兒童會害怕得不到相信、被圈子排斥。為了夢想與已經投放多年的努力,不少受害兒童寧願適應性侵的條件,即使代價沉重。
在某些處境下,天賦的才華也會使兒童成為脆弱的群體。社會大眾也常忽略高成就的兒童及青少年面對性侵時的脆弱性。
理解風險,為了保護兒童
兒童性侵從來不是受害者的錯誤。成人加害者需要對他們的行為負上絕對的責任。在校園、育幼院、教會等機構內發生的兒童性侵事件,機構則有責任確保兒童在他們的照護期間的安全與福祉。書寫性侵事件的兒童脆弱因素,是為了理解性侵加害者如何挑選目標兒童。我們不是把責任放在受害者身上,而是我們需要理解加害者如何利用兒童的脆弱性,從而更敏感更積極的保護我們身邊所有的孩子。
註四:Sullivan, P. & Knutson, J. (2000). Maltreatment and disabilities: a population-based epidemiological study. Child Abuse & Neglect, 24. p. 1265.
註五:Robinson, S. (2016). Feeling safe, being safe: What is important to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with disability and high support needs about safety in institutional settings? Lismore: Centre for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 p. 76.
 陳潔晧、徐思寧/《蝴蝶朵朵》繪者
陳潔晧、徐思寧/《蝴蝶朵朵》繪者

本文出自人本教育札記340期


2023工作報告_玩的教育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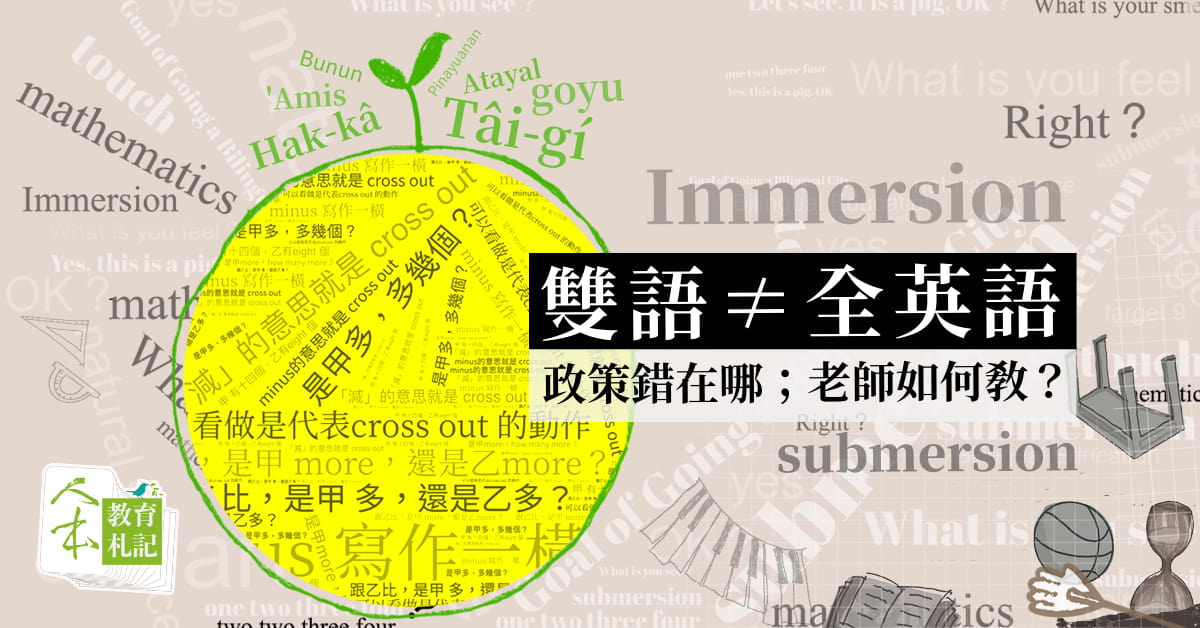
【專題】雙語 ≠ 全英語!──政策錯在哪;老師如何教?

GiveMe5 我不打小孩 家庭動起來記者會

打造愛的家,我不打小孩。台灣兒權向前行!我們可以!

快樂父母班

社會賢達共同支持教育轉型正義,小英總統蒞臨人本募款餐會
人本教育基金會年度募款餐會「聚賢會」今日(10/19)順利舉行。蔡英文前總統親臨現場,與陳建仁前副總統、立法院多位委員、教育與人權倡議者、藝術家、以及公民團體代表、各界及社會賢達,共同為「教育轉型正義 全民抗網保孩」等工作籌募資金,現場氣氛熱烈,昭示教育改革信念堅定,能量持續。
曲解數據,混淆政策改善,於教育不利。全教總不要只想著廢,總該有調查監督機制吧
每年接受校事會議調查的教師,僅占不到千分之六。這樣的比例在任何工作領域中,都難以被稱為「浮濫」,反而應視為制度運作下的常態監督,是確保專業與倫理的基本機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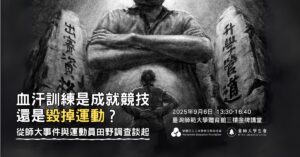
【座談會】血汗訓練是成就競技還是毀掉運動?─從師大事件與運動員田野調查談起
為深入了解台灣體育班制度下學生運動員的真實處境,人本教育基金會邀請16位曾為體育班學生,及一位現職體育班運動防護員進行焦點訪談。受訪者跨足棒球、足球、田徑、籃球等多項運動,年齡層自18歲至39歲,以呈現了體育班制度長年存在的系統性問題⋯⋯

強迫抽血惡師免解聘!?台師大血汗學分,教育部置身事外?
去年 11 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競技系教授周台英被指控於國科會「建構新世代精準女性足球運動生心理、傷害及表現的智慧感測與衡鑑平台」研究計畫中,以畢業學分強迫學生擔任受試者進行抽血、試驗,並且將受試者費收走,甚至對不願配合的學生實施精神壓力與排擠行為。現經臺師大校園霸凌調查小組認定成立周師有七項霸凌行為屬實,對三成立,建議應予以解聘,並兩年不得再擔任教師⋯⋯

請新竹、花蓮縣府不要再漠視兒少安全運動教練不適任制度也需立即建立
兒少在運動訓練過程中,遭到身心暴力,性暴力的事件頻傳。人本近期,又接到兩件申訴案。顯示不論學校外聘運動教練還是民間館場,目前教練不適任制度,仍有巨大法規漏洞,也有執行端的怠惰與混亂⋯⋯

你們挺暴力,誰來挺小孩?!校方縣府聯手放水,我們要求依法處理
本會接獲家長投訴,去年(2024年)2月他們向雲林縣西螺國中申訴廖姓專任教師與蔡姓兼任教練嚴重體罰與霸凌羽球隊學生,校方和縣府疑似輕放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