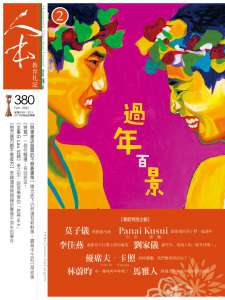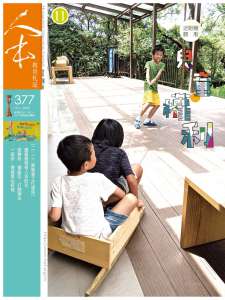應許之地,如何成形?
〉與老師及校友、家長對談

本文出自人本教育札記第347期〈性騷擾者的應許之地—細看屏東某校性騷案〉
肢體騷擾、言語騷擾、利用權力的騷擾,以及男對女、女對女的騷擾…一般人想得到的各種性騷擾樣態,屏東這所高中幾乎都出現了。
一朝一夕,不可能如此。我們不由得要想。
事實上,該校成為性騷擾者的「應許之地」,還真的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該校立校時間雖然不久,卻也已足夠讓有心的老師、校友、校友家長觀察到一些長期存在的現象—一些應許之地所以能成形的現象。
師生分際模糊
其實一開始,我們只聯絡到R老師,希望從他那邊,我們可以瞭解事情如何發展到現在的地步。
R師曾在該校任教多年。要說「曾」,是因為他已離開該校。「不滿校園風氣而轉校的老師,數量滿大的。」R師表示:「就是校風不良啦。」此處所謂校風,主要是指學校裡發生的那些—用R師的話來說—獵奇的事。
R師告訴我,從他一進學校,就不時會聽說有男老師在夜晚將女學生載出門,很晚才回來。他原本還覺得只是傳聞,但「後來我從學生那邊知道,有的老師會頻繁地在課堂上以女性性器官當成『舉例』,而他的課與生物、性教育無關。」R師繼續說:「我甚至看到,有男老師和女學生會碰觸彼此的身體,不只是拍肩膀摸頭喔,是輕拍對方的屁股!」幾件事湊在一起,他開始感到有點不對勁。然後,他聽到另一個更糟糕的傳聞—有老師以班聚為由,約同學們去老師家聚會,會後將少數同學留下,或帶往其他場所過夜。
「從一群人裡挑出少數人過夜?當自己是古代皇帝嗎!」我脫口而出;R師聽了,並沒有責怪我衝動或比喻不當,而是說:「那些人實在太過份,所以我問了傳這些事的同事們怎麼看?」R師之所以問,也有想循線追索的意思。但同事的反應,讓他追不下去。「他們說,就是那幾位老師受學生歡迎啊,有什麼問題呢?他們一點都沒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R師停了一下,才又說:「那間學校任用非常多年輕的老師,教學經驗不夠,因此無法判斷某些行為是單純的受學生歡迎,還是已經踩紅線。再加上教師這個群體,大多數人存著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態,覺得一旦管太多、得罪人就不太好。」言下之意,他們會下意識地往「沒問題」的方向去想。
偶像崇拜
那麼,學生呢?沒有學生覺得同學被挑出來在老師家過夜怪怪的嗎?「老師們年輕,很容易可以跟學生打成一片,很多師生之間沒有距離,更像是朋友。這有好有壞。」R師分析:「在這些沒社會經驗的學生眼裡,老師們各個年輕又充滿個人魅力,因此常聽到學生把老師當偶像崇拜甚至追捧;所以就算他們有人聽到傳言,也大多認為只不過是那個老師太受學生歡迎了,真的不覺得有事情正在發生。」
然後,R師說:「多數同學們講述這些事情時,不只都不覺得怎麼樣,有些還會覺得是老師額外給的福利或是照顧。」
學生社會經驗淺,對大人有偶像崇拜的心情可以理解;然而,老師身為成年人,又肩負著保護學生的任務,實在不能不留意這中間的危險、不能不拉出界線—否則,拍屁股、夜半出遊或過夜這類的事如果被有心人利用,甚至有心人刻意製造「那又沒怎樣」的氛圍,學生不就成了獵場裡的獵物?
同儕壓力成為加害者護盾
談到這裡,我發現R師時不時瞄瞄手表、看看門外。「應該要來了吧?」R師說:「有一個同學和他媽媽,可以告訴你所謂『受歡迎的老師』做了什麼事。」過了一會,我聽到敲門聲;R師開門,走進來一對母子。就姑且稱他們S同學和S媽媽吧。
R師向S同學說:「講講那個音樂老師的事吧。」看樣子,他們已經討論過今天要講的內容。
「蛤?一來就要講喔?我剛騎車很累捏!有沒有飲料?」S同學攤在椅子上。
「騎車的是我吧?你累什麼?終於有人注意到你們學校那一大拖事,你還不快講?不喝飲料不會死啦!」S媽媽碎唸兒子。
S同學大笑,然後說:「那個老師喔,大家都說他很會教、人很帥就,很多同學喜歡他啦。」他停了停,表情似笑非笑:「不過,有時候午休我去幫導師拿東西,經過音樂教室,會看到有女同學跑進去找他。我跟同學講,他們有的說我滿腦子就想這種很A的事,有的說大概就是找老師問事情,老師那麼好,不要亂講話。」
「不過,慢慢的,有幾個同學告訴我,他們也發現一樣的事。而且去找音樂老師的,就是特定幾個女同學而已。八卦是,那幾個女同學平時上課多少會聽一點,可是只要午休去找音樂老師,下午的課幾乎都趴著睡覺,很累的樣子。」男老師與女學生在全校休息時,到音樂教室獨處?事情太可疑了吧?當年學校知情嗎?有處理嗎?
「我們那時沒跟學校說,覺得壓力很大。」S同學告訴我。R師補充:「S同學他們畢業幾年後回來找我,我才聽他們講的。應該是沒有同儕壓力,比較敢講。」確實,少數學生要指出受歡迎的老師犯了錯,必須面對的同儕壓力,光想就讓人卻步。然而,學校可沒有這種壓力!事情發生不只一次了吧?校方是始終不知道,還是另有隱情?
「至少,學校知道其中一部分。」R師的意思是,拍屁股、留過夜、不當的性舉例、音樂教室獨處這一大串事情,學校知道一些;而之所以只能含糊地說「知道一些」,不能確切地講「知道哪一些」,是因為學校的反應也相當含糊,如R師說的:「校方有在開會時,口頭講過幾次要老師小心界線之類的話,但不具體說發生了什麼事,甚至連積極地規勸那些老師也沒,所以沒有什麼成效,過一陣子就又會聽說類似的事情再度發生。」
沒有專業監督機制
「對啊,像那個上課會講她跟老公怎樣怎樣的老師,就一直那樣啊!」一直沒說話的S媽媽開口了:「就是,講她跟她前夫怎麼談戀愛怎麼做這個那個最近我還聽我兒子說,學弟告訴他,那個老師在課堂上要大家幻想另一半摸自己。」S同學接過媽媽的話:「這個只是聽說啦,不要講這麼確定啦。」媽媽回:「不是說教育部有來查、學校還發問卷下去問嗎?我覺得我不是這方面很保守的家長,可是,性教育應該要有專門的老師來教吧?她的科目明明跟性教育沒有關係啊!而且就有學生說感覺不好了,這樣算不算性騷擾?」
R師嘆了口氣:「我在那裡的時候,校方沒有任何制度去追蹤或說輔導、協助老師上課的內容。老師們想上什麼,基本上都是他的教學自由,這有好有不好。像媽媽說的事,就會被說成『創新的教學型態』。我想,校方到現在應該也沒建立相關機制;校方應該要拿出辦法來,該有一個機制約束老師們不該逾越上課內容及注意師生分際。」
息事寧人之風盛行
「可是,怎麼會學校裡沒有任何老師對他們提出意見?」我問:「我指的是,有些老師可不只是上課內容太誇張而已,根本涉嫌性騷擾了啊!」R師看來想回應,但S媽媽快他一步:「唉唷,有哪個老師敢講?他們做那些事很久了,早就變成一國,其他老師就算覺得不對,也會私下講講就算了,要是提出來講,被針對了怎麼辦?」
「其實真的比較多人覺得沒發生什麼事,就像前面我說的那樣,學校有個氣氛在。我也像媽媽說的,私下講一講、問一問,就沒有繼續了,最後受不了就離開…」R師說著說著,聲音低了下來。個別老師要對抗整間學校的文化,本來就不容易,選擇離開,也算是一種無奈吧。然而有的人是不能隨意選擇要做什麼的—比如校長,他理應不能選擇無視。
S媽媽一貫快人快語:「校長?他們有什麼用?換了好幾個校長,每個都嘛想趕快調學校!我們這間就不是名校啊!」S同學似乎不同意:「幹嘛這樣講?上一任校長還可以吧,R老師也說了,他會宣導不要亂來。」R師對他們笑了笑,說:「校長他們是沒那麼糟啦,我相信他們再怎麼樣也不會真心覺得那些老師做得對。可是,壞就壞在他們選擇息事寧人,說一說就以為問題可以解決、以為可以再相信那些老師。這只能暫時解決問題,因為那個信任很薄弱,肇事者沒有付出代價,再犯機率很高,信任隨時會被他們的再犯瓦解,異常的事就會不斷發生。」
應許之地,應許給誰?
種種現象,個別來說都不足以使該校形成今天的局面:如果老師們好好抓住分際、如果有人幫學生應對同儕壓力、如果有一位校長不輕易放過性騷擾的老師只要其中一個現象被破除,事情就會有所不同。
但實際上,校方缺乏任何有效的作為,甚至缺乏事態嚴重的認知,而放任個別有意識的師生陷入無從施力的泥淖之中,從泥淖中,就浮起了性騷擾者的應許之地。
應許了性騷擾者的學校,還能應許學生嗎?還能應許教育嗎?
- 特別企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