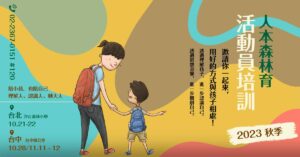自主學習:「自主、實驗」VS.「主體、理念」


在台灣,講起理念教育、實驗教育、體制外教育……等等,很難不談「自主學習」。這看起來理所當然:如果說傳統體制教育最大的缺失之一就是強迫小孩學習,那麼要反抗體制教育,就得反抗強迫學習,而既不強迫,不就是「自主」嗎?進一步來說,真正的學習絕不可能強迫得來,人要是不真的想學某事,學習的效果往往只限於表面,可以說根本算不上是學習;就此而言,「自主」當然是「學習」的必要條件。
就像人本董事長史英老師在本場次開頭說的:「自主學習是現在的重要概念,因為已進入新的課綱,會變成全國教育發展的重要概念。」過去,自主學習是對抗傳統體制教育的重要概念,而如今它已被納入體制,所有的教育工作者,無論身處體制內外,都沒有不思考它的空間。然而,史老師提出了重大疑問:「在體制內有令人憂心的狀況:沒人討論自主學習是什麼意思。所以從一個極端,把小孩用無形的鐵鍊綁著強迫學習,到另一個極端,小孩不學沒關係,我們等到他願意。這樣到底對不對呢?即使是對,可以稱為自主學習嗎?」
本文將以史老師的提問為核心、以會中討論的幾個要點為脈絡,為該場次研討會寫下紀錄,至於會中提到的眾多教學實例,礙於篇幅,只摘其中幾個,無法全部收錄。
贊同學生有自主學習能力,就該完全放手嗎?
事實上,傳統的體制內教育並非完全沒有自主學習。與談人,宜蘭縣立員山國小吳仲堯老師就認為:「大家都說自主學習是比較進步的,體制外的。但其實體制內的,對他們覺得不重要的事,已經給了自主學習的空間。」
仲堯的發言來自切身經驗。三十多年前,身為小學生的他是體制教育的得勢者,成績好、常得獎,體育也很不錯。「檯面上我是老師眼中的模範,學校的寵兒,私底下不是這樣子。」他說:「我很愛打球,跟一個大我四五歲的大哥哥學了很多運動,到校後就找同學打球。到了五年級,老師沒辦法駕馭我,因為老師不會。我們當時就踢足壘球,都是我在制定規則,老師在旁邊看。不只體育課強迫人陪我學習,也在其他地方找人陪我學習。體育弱的人,我常霸凌他們,拿球丟他說他在搞什麼。」
「老師不曉得是看不到我的行為還是不看。」仲堯繼續說:「同學對我累積了不滿情緒。六年級時,我是負責吹哨子糾正同學的隊長,有一次我還沒吹,副隊長就吹了,我就不爽,罵他,引爆同學對我累積的不滿。以前是我在排擠人,現在是人家排擠我。後來我下課一個人不知道要幹嘛,是弱勢的、不太會的同學來陪我講話。那時我得到挫敗,知道世界不是圍繞我一個人的。」
「仲堯在學校自主發展,能力也好,可是在那過程裡要面對很多人的不會,而他不懂怎麼面對,就用很多方式去『處理』。」森小生活主任謝淑美接過仲堯的話:「可是他有能力處理嗎?小孩學不會,連大人都覺得很難處理了,卻要他自主學習,不免變成他強迫別人學習,使兩邊的小孩都付出代價。」
「人本透過梯隊、申訴案,看到太多在這過程中受害的小孩。有孩子一直戴口罩,或夏天穿長袖,因為他在團體裡沒安全感,所以只好隔離自己;或是,把自己裝得很強,去欺負人,讓人不會欺負他。」淑美說,這些孩子往往來自標榜「自主學習」的環境;顯然,大人完全放手,號稱讓孩子自己學,其結果是淑美說的:「我們希望孩子能學會的,不見得有在發展,但不希望他會的,往往在發生。」關於這點,森小老師何淑真(小何)說得很明白:「我們不想要以前那個強迫的方式,希望孩子有更多空間、教學者有更多空間。我也有過這種夢想,讓孩子自己去學習,但一開始不太會教,對小孩也不夠理解,教學時以為給孩子很多空間就是最好的方式,或是一直問孩子問題。但其實小孩什麼都不會時給他空間或問他繁瑣的問題,會使他焦慮、混亂。」而以小何的經驗,孩子們通常很善良,知道大人不想強迫他們,會配合演出自主學習的樣子,好像有在思考、有做點什麼,但事實上心裡無所適從;不知道怎麼辦,又想配合大人,就很容易做出與課程無關的行為,或是與提問無關的回應。「這時大人會受打擊。我做錯了嗎?他們竟然給我胡鬧、亂講答案!?」小何說。
學生有能力自己學會一些事,無庸置疑;但若因此就完全放手,美其名為「自主學習」,很可能產生種種偏差,而學習未必發生。

自主學習 vs. 主體性學習
可是,如果不放手讓小孩自己學,會不會走回「強迫學習」的老路?淑美在研討會上舉的一個例子,可供參考:「森小有個孩子在幼稚園時,不會寫字老師就打,所以他來森小後怎樣都不想寫字。我們一開始就讓他不寫,但兩年後,他還是不寫。於是我們跟他談,到底現在有什麼困住你?談了之後,他可能是把自己的狀態想清楚了吧,就肯寫字了。」淑美看著台下聽眾,問:「如果我們不跟他談,他還要困住多久?談過之後,他肯了。這當然沒有強迫。然而,他需要被協助,才能走過心裡那個『不想寫字』的問題。」
孩子還小,很可能意識不到自己之所以不想寫字是被過去的經驗困住了;以他為主體,大人應該思考:他是真的被困住嗎?如果是,可以怎麼幫助他脫困?淑美又舉了一個常見的例子:小孩想留在學校跟同學玩,卻也想回家,他不知道怎麼選,很困擾。「他說不出個道理來,可是困擾的感覺好真實喔。這種兩難下,我們怎麼幫小孩去做出選擇?」淑美說:「所以才需要有大人。不然,幹嘛要有父母和老師的存在?」孩子還小,經驗不足、思考能力還在發展,因此需要大人協助他去判斷眼前的事務、去學習。這當然不是強迫,而是──用淑美的話來說──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
這種「主體性的學習」,才是「自主學習」的要點。就如小何說的:「要想像小孩現在的心智狀況,來發展適合他的教學方式。」她回憶起自己當年剛開始教書時,曾經設計過的教案,「我覺得中國文學有一個美好的主題叫『等待』,王寶釧等了十八年……我唸了余光中的〈等你,有雨中〉,我的同事們覺得好美喔,但是唸給小孩聽,他們還沒聽完詩就跑光光,他們接收不到。」如果在傳統體制教育裡,配合種種校規、生活公約,小孩非得聽小何唸完詩、同意等待的美好不可,強迫學習就出現了。然而,在森小,沒有體制裡那些威脅利誘,小何當年的教學既然沒能呼應到學生的主體,那就是失敗作收,即使她再如何不肯放手,就是強迫不來。
「比較好的教育,就像貼近大自然的花園,裡面就是不同的植物生長,該開花的、該長成大樹的,就順著性子自然伸展出去,不彼此扞格,這才是我心中的教育圖像。」這個詩意的描述,出自基隆市立八堵國小黃毓杏老師之口,她進一步說:「而且,不是每棵植物都會自己長出來的,有的會先附在別的植物身上。」植物順性生長而不受阻撓,一如學生就自己主體的需要來學習而不受強迫;但有些植物一開始無法自行生長,要先藉別的植物之力來發展自己,就像學生在許多時候要先靠師長的引導,往後才能走自己的路,這不能說是師長在強迫學生學習。恰恰相反,如果師長不出手,學習可能完全不會發生。
毓杏就主張:「我們八堵國小也在提倡自主學習課程,很多人誤會那個意思是在自主學習課堂上,學生可以做主,其他課不行。當然不是這樣。我們應該在國語數學等各種課程上跟學生建立一種關係:我身為老師,要給學生一些什麼,但在給之前要瞭解學生的胃口。」考慮學生的胃口,調配適合他的知識菜單,這當然不是強迫餵食,而是精心設計,要使他學習的胃口大開。「當然,我們要面對學生可能不吃。我常常被學生挑戰啊!教書這麼多年了,還是可能小孩不買帳,站起來說很無聊。」
「總之是,每次我們教下去踢到鐵板,比如班級秩序很亂,或是班級秩序太好…還有各式各樣的鐵板,只要踢到鐵板,我們就回來檢討,重新安排教學。」史老師回應:「自主學習就是反對強迫學習,抵死反對,但不能走到另一邊說都給學生決定要做什麼,這樣就對了。」
老師介入學習之必要
本場次進行到這裡,時間已將近一半,與談的眾人對「自主學習」提出許多論述,道理聽起來都很對,但有沒有具體實例呢?透過研討會的線上提問系統,不少聽眾都問起「實踐」的問題。
「如何在體制裡實踐?我試過太多蠢事。」仲堯首先回應:「我曾經在綜合課給孩子十分鐘放風,讓他們在校內愛幹嘛就幹嘛,結果有三個人走出教室鬼吼鬼叫;我想讓他們去體會到邊界,學校不是只有我們,可是他們當時是不是想過?我也弄過學生法庭,結果是投訴狀一堆,開不完的法庭;可是他們有沒有學到更好的與人互動的方法?沒有,衝突的時候就告來告去,只會在表象一直找證據,永遠沒完沒了。」
經過種種嚐試,仲堯的心得是:「我們常常覺得不要教訓小孩,所以當他發生事情時,應該讓他自己體會到他錯在哪裡、想讓當事雙方去互動……但我後來的心得是,為什麼這麼慢才要去處理,可不可以在沒出事前就下功夫?」換句話說,如果我們確切知道孩子的發展會需要某些思想、某些知識,為什麼非得等事到臨頭,才說要「放手」讓他自己去「學習」呢?以人際衝突為例,「事前,你有感而發地、一點點去講,幫他做思想實驗,辯證他的價值觀、帶他想跟人相處互動的技巧,是不是就避免、解決了一些問題?」仲堯說。很明顯地,他的思維並不是「自主學習」表面上的那一套──讓小孩自己去解決衝突──而是更核心的「主體性學習」──以小孩為主體,知道他們勢必要面對種種人際衝突,於是設計課程,帶著小孩思考可以如何處理糾紛。
淑美也舉了一個學生衝突的例子:「森小曾經發生過,有個六年級的孩子說一年級的一個小孩鎖了門,讓他進不了寢室;一年級的說沒有,為什麼要冤枉我?兩個人吵起來。」如果用學生法庭來處理,如仲堯說的,就是互相提告、找證據;許多人相信這能使學生自主地學到如何調解糾紛,但是一年級的孩子連話都還說不清楚,怎能在法庭上主張自己的權益?又怎能學到事理?
而淑美處理的方式是:「一年級的孩子覺得很冤,來找我,我先安撫他的情緒,然後跟他說,六年級的確實很有可能冤枉你;原因一個是他故意的、一個是他弄錯了,你覺得有可能是他弄錯嗎?他說有。我說:『那如果是這樣,你覺得這樣是不是你也冤枉了他?』他突然說,那我是不是要跟他道歉?」對這位一年級生來說,正因為淑美的介入,他才能意識到自己的盲點,這顯然是有所「學習」,而既關乎他的「自主」感受,更是切合他的「主體」狀態,又絕無「強迫」。
其實,要真正達到自主學習,老師該做的何止「介入」?有時甚至得「勸誘」。史老師就說:「自主學習不能只看學習發生之前有沒有人介入,主要看的是學習的過程裡面發生什麼事。很多學習,一開始是被老師勸誘的,但如果老師知道這個勸誘是為了要給學生什麼,那麼手段都是小事。
自主學習上,大家都太在意小事了:瑟谷堅持不對小孩說之以理,但老師都不去講的事情,小孩會主動跟你學嗎?小孩沒經過文明的建構,他是個純真的人,怎麼會自主?」這麼說,並不是不相信小孩有自主能力,而是考慮到一個現實的問題:小孩沒接觸過人類既有的文明,要怎麼知道文明裡頭有什麼是他想學的?連要學什麼都還不知道,又哪來自主可言?
小何以她的教學經驗為此下註解:「真的需要先把小孩勸誘進教室。我自己上小一的注音,聽到上課,每個人都說不要。準備很多好聽的故事,把他們吸引進來,談為什麼要學注音,幫他講心裡的感覺,比如『注音離你好遠好遠,你不知道幹嘛要學,對嗎?』然後,第一堂教一點點,讚美他們很厲害。」小何邊說邊笑:「就半哄半騙,他們後來發現進教室可以聽故事、學一點好玩的東西,就願意進來…」一開始是勸誘,然後是各種設計,配合小孩的心智狀態,讓他們感覺到學習的有趣之處,最後小孩的自主能力便能迸發。

實驗教育 vs. 理念教育
從實例來看,便能明白老師非但不能對學生的學習消極放手,還應積極介入。站在學生的角度,老師的介入,可以為學習指出更明確的方向、更深入的目標;當然,學習之所以能明確與深入,是因為顧及了學生的主體性。
另一方面,站在老師的角度,介入學生的學習也有深刻的意義。仲堯就說:「一個人的學習我覺得是不可能不受他人影響的,如果是這樣的話,是老師比較會影響學生,還是學生比較會?老師懂的比較多還是學生懂的比較多?顯然是老師。那麼,為什麼要放棄影響學生?你有沒有真的愛你的學生?如果有,為什麼不把你喜歡的東西分享給他?你有沒有真的愛那個學問、那個價值、那個知識?如果有,不是會很想分享給別人嗎?
所以,你說不要介入小孩的學習,說這是要讓他自主,不只是抑制了小孩,也抑制了自己,放掉了他也放掉了自己,不是很可惜嗎?」
身為老師,進入校園時,原本就帶著比學生更多的知識,也自然地擁有更多的權威。過去,體制教育往往是靠著老師的權威,把經過篩選的知識灌進學生的腦袋,以為這就是學習;後來,人們對權威有了警覺,因而認知到灌輸知識不構成學習,這就成了「自主學習」呼聲的源頭。然而,如仲堯說的,為了害怕強迫學生就什麼都不做,其實是放棄了自己擁有的知識、放棄了自己對知識的熱忱,更是放棄了學生。
也是因為對權威的警覺,許多人──例如瑟谷、夏山等體制外學校──會主張師生地位要對等;事實上,本場研討會就有聽眾提問「老師是否能放下教師跟孩子不對等的位階?」對此,史老師的回覆是:「希望師生對等,是天真的幻想。但這個想法有背景,因為過去受不對等的殘害太大,想扭轉。但老師的年紀這麼大,有這麼豐富的背景,怎麼可能對等?
我們應該說,不要去壓制小孩就好。為什麼要用『對等』這種抽象的名詞?老師叫小孩罰站,不行嘛,為什麼要用抽象名詞來套?再比如『自主學習』這個抽象名詞,用意是要反對強迫學習,那就反對,為什麼要用這個名詞?弄得不明就裡的人,連要鼓勵小孩學習都不敢?我的心得是,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不敢跟體制作戰!」現今的台灣,跟體制教育作戰的人,當然頗有一些;但也有許多人,抱著「自主學習」、「師生對等」,甚或是「翻轉教育」……等等抽象名詞,聲稱自己與體制教育不同,卻不細究其內涵、不批評體制的缺失,這就給了陳腐的體制一個可鑽的漏洞,「人們說要改革,體制就弄個『實驗教育』,人們抱著實驗教育就做了,體制教育就可以愛幹什麼就幹什麼。」史老師進一步指出,「實驗教育」可視為體制逃避改革的一個花招。
仲堯贊同史老師的主張,認為不要執著在「實驗教育」名詞上:「一群學生在我們眼前,我們認為對的理念,就教下去;這就是理念教育,就該這樣子,而不是什麼翻轉、做實驗。可是,這樣有強迫學生嗎?學生馬上可以舉手提問、走人。而且,我不斷精進教學、從學生的主體出發,一旦我可能意識到歪掉了,就修正。教學過程,不管在體制內外不都是這樣子?為什麼要另闢門路,提出各種抽象名詞?」確實,身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如果你對知識有熱情、對學生有愛、對價值有堅持,而隨時能虛心地反省各種在學生身上踢到的鐵板、不斷修正…你為何要自認你的教學只是「實驗」,而不堂堂正正地宣揚你的教育「理念」?
史老師為本場次做的結論是:「可能的話,我們要把台灣的前途交在小孩的手上;但在那之前,我們要先讓我們的小孩當台灣的主人。」而在讓小孩當台灣的主人之前,或許每位現場的老師要為了小孩,落實教育理念,當教育的主人!
 王士誠/人本教育札記主編
王士誠/人本教育札記主編
本文出自人本教育札記340期
- 相關文章推薦


2023工作報告_玩的教育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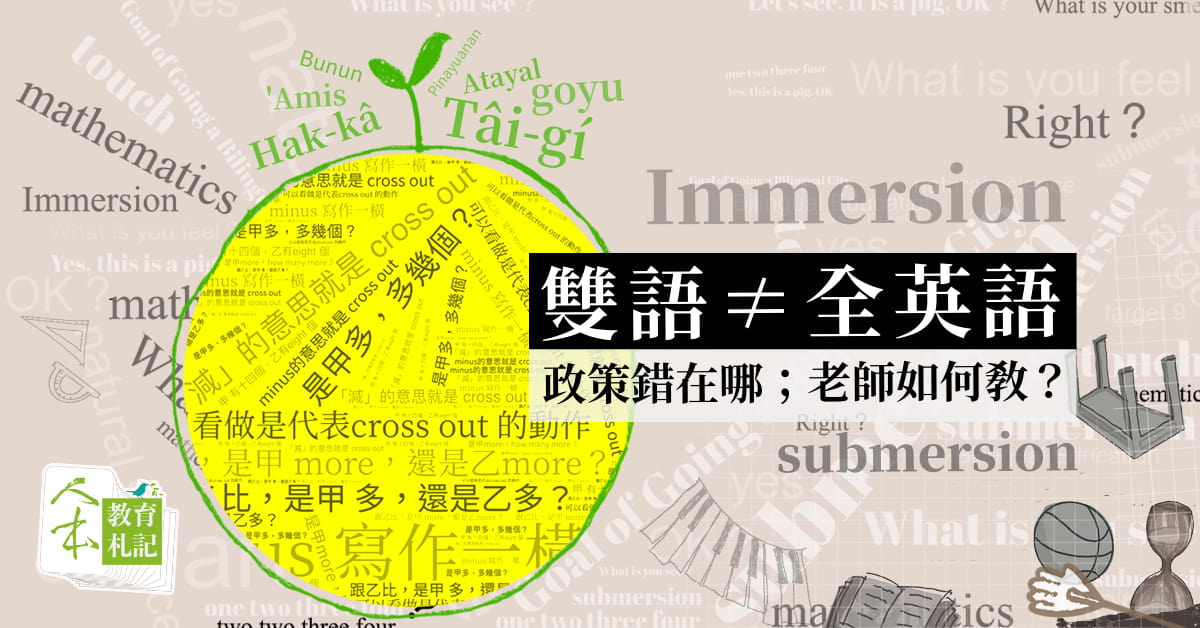
【專題】雙語 ≠ 全英語!──政策錯在哪;老師如何教?

GiveMe5 我不打小孩 家庭動起來記者會

打造愛的家,我不打小孩。台灣兒權向前行!我們可以!

快樂父母班
- 最新文章

社會賢達共同支持教育轉型正義,小英總統蒞臨人本募款餐會
人本教育基金會年度募款餐會「聚賢會」今日(10/19)順利舉行。蔡英文前總統親臨現場,與陳建仁前副總統、立法院多位委員、教育與人權倡議者、藝術家、以及公民團體代表、各界及社會賢達,共同為「教育轉型正義 全民抗網保孩」等工作籌募資金,現場氣氛熱烈,昭示教育改革信念堅定,能量持續。
曲解數據,混淆政策改善,於教育不利。全教總不要只想著廢,總該有調查監督機制吧
每年接受校事會議調查的教師,僅占不到千分之六。這樣的比例在任何工作領域中,都難以被稱為「浮濫」,反而應視為制度運作下的常態監督,是確保專業與倫理的基本機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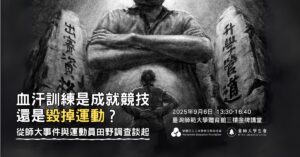
【座談會】血汗訓練是成就競技還是毀掉運動?─從師大事件與運動員田野調查談起
為深入了解台灣體育班制度下學生運動員的真實處境,人本教育基金會邀請16位曾為體育班學生,及一位現職體育班運動防護員進行焦點訪談。受訪者跨足棒球、足球、田徑、籃球等多項運動,年齡層自18歲至39歲,以呈現了體育班制度長年存在的系統性問題⋯⋯

強迫抽血惡師免解聘!?台師大血汗學分,教育部置身事外?
去年 11 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競技系教授周台英被指控於國科會「建構新世代精準女性足球運動生心理、傷害及表現的智慧感測與衡鑑平台」研究計畫中,以畢業學分強迫學生擔任受試者進行抽血、試驗,並且將受試者費收走,甚至對不願配合的學生實施精神壓力與排擠行為。現經臺師大校園霸凌調查小組認定成立周師有七項霸凌行為屬實,對三成立,建議應予以解聘,並兩年不得再擔任教師⋯⋯

請新竹、花蓮縣府不要再漠視兒少安全運動教練不適任制度也需立即建立
兒少在運動訓練過程中,遭到身心暴力,性暴力的事件頻傳。人本近期,又接到兩件申訴案。顯示不論學校外聘運動教練還是民間館場,目前教練不適任制度,仍有巨大法規漏洞,也有執行端的怠惰與混亂⋯⋯

你們挺暴力,誰來挺小孩?!校方縣府聯手放水,我們要求依法處理
本會接獲家長投訴,去年(2024年)2月他們向雲林縣西螺國中申訴廖姓專任教師與蔡姓兼任教練嚴重體罰與霸凌羽球隊學生,校方和縣府疑似輕放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