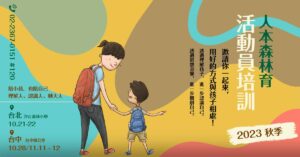森小的一堂國語課--〈桃花源記〉


很多人都說,陶淵明是思念家鄉「田園」,想要回家種田。不知道為什麼,在那一刻我突然體會了:陶淵明的「田園」不是真正的田地。
想像陶淵明當彭澤令的時節,家鄉的田地可能有親戚佃戶幫他種、或者沒有人種,無論如何田地都不會是「將蕪」的情況。「將蕪」是一種心頭「即將荒廢了」的感覺。穿越時空一千多年,我好像領會了陶淵明的「覺察」、「覺醒」。帶著這個心情,讀陶淵明的作品,會發現他說的桃花源、五柳先生,和一般人想像的,並不一樣。
如果說陶淵明寫文章只是想要表達「避世隱居」的願望,那他為什麼還要寫呢?

那天,跟大靖、阿翰一起在辦公室聊天。
大靖嘆了一口氣:「哎喲!快要畢業了。真討厭!為什麼森小沒有國中?」邊說著,雙手抱頭埋到兩膝之間,一副想要「逃跑」的模樣。
「你到底是來森小『逃避』?還是來『追求』的啊?」我問。
大靖猛抬頭:「我當然是來『追求』的啊!」
「那就不要怕,去面對它或改變它。」
「好啦好啦…」孩子有點不好意思再說什麼。
一旁阿翰幽幽地接口:「但是以後到國中,我就會被改變了啊!」
國中,像一隻酷斯拉,已經暗暗地撲向六年級孩子的心頭。
我慢慢地說:「嗯。你可以選擇要被國中改變,或者去改變它。走吧!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要去上課。」
孩子來上體制外小學,到底是追求,還是逃避?我想問他們這句話,已經一年了,今天終於「時機成熟」。而為了鋪這句話的「梗」-孩子要能聽得懂-我連上了兩個星期的〈桃花源記〉。
► 文言文好?還是白話文好?
〈桃花源記〉是一篇高中課文,小學生到底能不能閱讀這麼深奧的文章,如果說我心底沒有一絲一毫猶豫,那絕對是騙人的。我知道,在台灣,人人心底對這些「聖賢文章」有莫名恐懼。為了鼓舞孩子們正面迎戰心頭的怪獸,我把高中國文課綱的戰火,先在國小課堂上點燃了。
第一堂課我先跟孩子們說起了前陣子的大新聞:課本裡到底是要多放幾篇文言文?還是白話文?
這個問題拿來問小孩子,答案只有一個:「廢話,當然是白話文啊!」
「白話文有什麼好?」我問。
「生活化!」「活潑!」「實用!」孩子們回答得比五四健將還流暢。
我忍不住問他們,如果白話文這麼好,為什麼學者專家們不要多放幾篇呢?請孩子們試著揣摩看看,文言文有什麼好?
「是中華文化的精髓!」一個孩子說,一群人頻頻點頭如專家學者。
「說得真有道理啊!」我微笑著:「請問小學課本裡是文言文?還是白話文?」
「全部都是白話文啊!」才剛說完,孩子們個個表情突然凝住了。
「這些白話課文有『生活化』、『活潑』、『實用』嗎?」我故意慢吞吞地問。
「沒有!」孩子的回答倒很乾脆。「重要的都被刪掉了!」
「形式是新的,內涵是舊的。」一個孩子下了結論。
我順著孩子們的話,談到高中課綱的爭議重點,也許不是白話文、文言文的比例問題。依照目前編書者的思維,不論是哪一種文類,凡是有血有淚、「重要的都會被刪掉」,只留下一些八股教條的篇章。
「既然是這樣,我倒覺得多讀幾篇文言文也不錯。這樣可以好好弄清楚『內涵』出了什麼問題!反正…」我還在想著要怎麼接下去。
「知己知彼!」一個孩子接口。
► 先解字?還是先解句子?
孩子們心情上已經準備好要進入「古文」。我發下原文,請他們先針對第一句話提問。
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
「『晉太原』是什麼?」「『武陵』是什麼?」古文果然可怕,七個字裡就有五個叫人摸不著頭緒。我慢慢地說明什麼是「朝代」、「年號」,補充資料性的訊息。接下來的就很容易了,孩子們憑直覺能猜到「有人迷路了」、「捕魚的」。
在森小,讀白話文和文言文的手法是一樣的。孩子們直接一句一句地閱讀、提問。哪個孩子卡在哪個字,大家就停下來猜一猜,從前後文、直覺去推敲,大概都能「想出」句子的意思。先猜出一整句話的意思,再來猜想某個「字」的意涵。例如:「緣溪行」,孩子讀完就能猜出是「沿著溪走」,這時候再來斟酌「緣」的意思,孩子會發現,平常用詞是「緣份」「緣故」,細緻的想都有「沿著」的內涵。
一般國高中在教文言文,老師直接叫小孩背「註釋」,一個一個硬生生地背,忽略字詞原有的「內在意涵」的相關性,這恰好是殺死孩子對古文樂趣最快的手法。
也許有人會問,這樣教不會很慢嗎?進度不會來不及嗎?
以閱讀〈桃花源記〉來說,一段一段、一句一句地往下推想,大概只花了兩節課的時間,只比講解註釋和考試加起來的時間多一點點。孩子們整句整段的閱讀理解,速度超乎想像的快。讀完時,他們的臉亮亮的說:「沒有想像中的難嘛!」
► 〈桃花源記〉是夢一場?
解完整篇〈桃花源記〉後,我問孩子們,「桃花源」指什麼?
「是避難所!」「是學習所!」孩子們眼神亮晶晶地說。
「我覺得作者作了一個夢。」一個孩子沉思著。
「對!是一個白日夢!」「他幻想。」「瞎掰。」孩子們作出了決議。
孩子們這麼說,恰好反映老師教古文時,只教完「字詞理解」是不夠的。知道了字面上的意思,沒有對文章更深刻的追問,〈桃花源記〉在孩子心頭只是「夢」一場。
要怎麼突破日常思考的侷限、往更深處挖掘呢?我請孩子們試著提兩類問題。第一類是「為什麼是…,而不是…」。
我舉例:「為什麼主角是『漁人』,而不是『讀書人』?『南柯一夢』、『黃粱一夢』主角都是讀書人。如果『桃花源』是一場夢,為什麼主角是漁人?而不是作者自己?」
「對喔!」孩子們陷入沉思。
「再往下仔細想,水路上,最不容易迷路的,其實是…」
「漁人!」孩子說:「好故意喔!」「而且漁人不懂字。」他們慢慢意會了作者的「別有用心」。
我鼓勵孩子們再想一想,整篇文章還有哪些「為什麼是…而不是…」的疑點。班上一片靜悄悄。面對這樣特別的安靜,我的心像伏在暗處的一隻貓。
「為什麼不找到?」一個孩子打破了沉默。
「為什麼高尚士也找不到?」另一個孩子也問。
聽到這兩個問題,心頭的那隻貓咪想跳起來,我按捺著。再請孩子們想另一類問題:「作者寫了什麼?沒寫什麼?」
又是一陣靜默。
「沒寫村長。」「沒寫學校。」
按捺著喜悅,請孩子們猜一猜,為什麼作者沒寫?一個孩子說:「作者恨這些。」
我回想起自己當年在公務單位服務時,曾經重讀陶淵明的〈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很多人都說,陶淵明是思念家鄉「田園」,想要回家種田。不知道為什麼,在那一刻我突然體會了:陶淵明的「田園」不是真正的田地。
想像陶淵明當彭澤令的時節,家鄉的田地可能有親戚佃戶幫他種、或者沒有人種,無論如何田地都不會是「將蕪」的情況。「將蕪」是一種心頭「即將荒廢了」的感覺。穿越時空一千多年,我好像領會了陶淵明的「覺察」、「覺醒」。帶著這個心情,讀陶淵明的作品,會發現他說的桃花源、五柳先生,和一般人想像的,並不一樣。
如果說陶淵明寫文章只是想要表達「避世隱居」的願望,那他為什麼還要寫呢?
陶淵明寫桃花源記,既不是一場夢,也不是想表達「避世隱居」的願望,到底他為什麼而寫?
我請孩子們揣摩「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這句話背後的情緒。談到陶淵明生活在「東晉」,就好比孩子生活在「民國」,卻告訴別人「乃不知民國」或者「乃不知蔡英文」,這背後可能是什麼心情?是真的「不知道」,還是有別的想法?
「不值得知道。」一個孩子猜。
我接著問:「漢、魏晉代表的是什麼?」
「政府!」另一個孩子說:「他覺得政府不重要。」
我問:「政府真的不重要嗎?如果台灣沒有政府,就像森林小學沒有朱朱校長、青蘭主任,會發生什麼事?」
聽到森小的例子,孩子猛然一驚:「會天下大亂耶!」我忍不住偷笑,心裡想著,這群平日很會跟大人嗆聲的小鬼,心裡還滿喜歡有大人在的嘛!既然政府不是真的不重要,為什麼陶淵明要這麼說?延續這個疑問,請大家再看一次文章:在「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情況下,桃花源裡的人們生活過得如何?
「過得非常好!」孩子說。
這時候,很容易就能推敲出陶淵明的「言外之意」。我補充從東漢末年起,曹丕、司馬炎…直到陳宋改變東晉的國號,這一連串的政治風暴。陶淵明出生在貴族世家,先人陶侃立下樸實勤勞的家風(搬磚塊的故事),加上中國知識分子對於儒家理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期待,請孩子們試著揣摩,陶淵明身為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看著國號更迭、朝廷混亂、小人當道,對於「政府」的看法可能是什麼?
「他會覺得政府說一套,做一套。」孩子這話呼應了之前的猜想,陶淵明「沒寫村長」、「沒寫學校」,是因為「作者恨這些」。
這時我突然很好奇,忍不住問孩子:「你們再猜猜,為什麼最後陶淵明要安排找不到桃花源?」
思索的片刻後,一個孩子說:「因為他不想要桃花源被破壞。」
這答案到底對不對?我還是默默地收下,暫不回應。
► 為什麼「不足為外人道也」
討論「乃不知有漢」這大段的最後一句:「不足為外人道也。」在漁人要離開桃花源前,村民交代了這句話。這句話的言外之意又是什麼呢?孩子們猜得極有意思:「反正你們來不了」、「諷刺的意思」、「只不過沒有『政府』,沒什麼了不起!」,每句話的背後,都帶著豐富的情緒。
我談道「不足為外人道也」這句話如果套用在日常生活裡,可能有兩種情境:
第一種是A叮嚀B。比方說,A今天考試全部答對,他告訴B:「不足為外人道也。」這是什麼意思?孩子說:「不值得講。」我幫孩子把話補充得更清楚些,是「謙虛、委婉地請對方不要講」。
第二種是C問,D回。例如:D找到一個秘密基地,C問他:「在哪裡?」D說:「不足為外人道也!」孩子一聽馬上說:「這是不想跟你講」、「故作神秘」。
討論完這兩種語言的情境,請孩子們猜猜,陶淵明使用的,是哪一種語境?孩子猜:「第一種!」
這天課後,我和一群孩子在走廊上聊天。一個孩子沒頭沒腦地突然問:「森小老師的薪水到底是多少啊?」老實人如我,心裡忖度著該如何回答,只聽見另一個聲音悠悠地接口:「不足為外人道也。」接下來幾天,不論課後我問這群鬼靈精們什麼問題,他們時常流露詭異的微笑說:「不足為外人道也!」
► 為什麼太守找不到
經過前幾節課細緻的推敲,我們來到最後一段: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孩子提了新的問題:「為什麼是去找太守,而不是去找家人朋友?」
我高興地順著話說,對啊!如果是漁人想要「移民桃花源」,應該是要找家人朋友吧!為什麼找太守呢?
「他想告密!」「想討賞!」孩子們靈光的雷達打開了。這時才請孩子們回頭思考前面提的問題:「為什麼不找到?」思索這個問題時,要從對立面想:「萬一被太守找到,會發生什麼事?」
孩子說:「會統治桃花源」、「會有官府」、「要抽稅納稅」、「會管理教訓,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
我談起四百年前荷蘭人來到台灣這個「住滿原住民的桃花源」,除了招攬漢人來開墾,也藉口抽「萬萬稅」。等到鄭氏王朝來屯兵台灣,馬上就建立「孔廟」、書院。殖民政府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強勢入侵,從來都不手軟。
► 為什麼高尚士也找不到?
孩子們對之前提的問題,越來越能說出深刻的看法。關於為什麼高尚士也找不到?大靖很有把握地說:「因為高尚士被體制孕育。」我忍住心頭的狂喜,眼光溜了一圈其他孩子們的表情--堆滿莫名其妙的臉。我請孩子們追問大靖。
「關體制什麼事啊?」阿翰不解地問。
大靖思考片刻後說:「高尚士吸收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可能他也沒做到。」
「萬一高尚士都能做到呢?」阿翰不善罷干休。
「反正作者討厭那一套!」大靖也不退縮。
聽著這段交鋒,我高興極了!我知道,大靖是憑著對文意的直覺,深刻體會出來的,要他再說得更具體很難。我幫忙解釋,高尚士或許能做到體制要求的道德,但是他無法「反抗」不合理的事,他沒有自己的思想。一邊說,心裡暗自想著,社會上諸多能說善道的「高尚士」,遇到不公義的事情也是安靜無聲的啊!陶淵明寫〈桃花源記〉,特別要譏諷高尚士一下,也算是一種劃清界線吧!
談到這裡,請孩子們再想一想:「為什麼陶淵明要寫桃花源記?」
「他要說人民沒有政治、官府,也能過得很好。」孩子說得肯定。
► 是追求,還是逃避?
這下子,孩子的想法跟「避世隱居」這類消極的說法完全不同了。我終於能拋出最想問的一題:陶淵明寫這篇文章,究竟是要表達「追求」?還是「逃避」?
「我覺得是『追求』。」安兒一邊想,一邊慢慢地說:「陶淵明在說,人有自己的思想,你們的思想進不了我的世界。」
在小說頭兩頁,畫出來孤伶伶的,課文只摘取的幾行字。
請孩子們先忍住不滿的情緒,讀完這兩頁,觀察作者怎麼描述小樹和爺爺的互動?
小說一開頭是描述喪禮現場,大人們討論如何安置小樹,以及要分配小樹家的家私。在哀戚肅穆的場合裡,作者故意用「皆大歡喜」四個字,意味深長。接著,小樹和爺爺的目光穿越人群,找到彼此。小樹馬上推開人群、穿越院子,「緊緊地抓住爺爺的腿」,不肯鬆手!
「小說裡都有寫啊!」孩子們驚嘆,這麼重要的「有心肝」畫面,怎麼不見了?請孩子們猜猜,課文為什麼刪掉這些段落?
「覺得那不重要。」孩子說。
「不重要嗎?」我反問。
孩子們思考著。
► 吐槽課文第三招--猜想教科書編輯的苦心
一個孩子繼續追問:「為什麼小樹會安心的沉沉入睡」?
我請孩子們讀失落的另一段。大家驚訝地發現,小樹和爺爺奶奶怎麼「上公車」的過程也被刪去了。大家問著:
為什麼他們必須「等所有的人上車後才開始移動腳步」?
一個孩子突然聯想到,這裡頭會不會有「歧視」?我追問孩子,為什麼往這個方向猜?他一時說不清楚,純粹是從文字「憑感覺」看出來的。
孩子說不清楚,一來是因為作者故意寫得很曖昧,二來則是背景知識不足。再繼續追問的話,也不會有太多收獲;所以,是老師說故事、補充背景知識的好時候了。
先請孩子們「看清楚」小樹的爺爺奶奶是什麼族?孩子們發現,小說一開始就提到「查拉幾族」,一個沒有聽過的詞彙。第一次閱讀時,因為是沒聽過的名詞,眼光自然「跳」過去了。
我談道「查拉幾族」屬於美洲原住民印地安人的一族,就像台灣的原住民裡有阿美族、布農族,印地安人裡也有「查拉幾族」、「白族」…,是美洲大陸的「老祖宗」。
「是美洲的祖先,為什麼會被歧視?」孩子純真的追問。我說起歐洲人趾高氣昂地「發現新大陸」,正是印地安人悲慘歲月的開始。
一個孩子忍不住抱怨:「小何妳不要再講了,我本來很喜歡美國。」
我微笑著告訴他,美國的好萊塢製造很多正義凜然的人物,例如「美國隊長」,透過這些角色昭示全世界,美國人是「大好人」。在真實的歷史裡,美國人對印地安人、黑人並不公道,歧視、欺負他們,甚至奴役他們。這些事在台灣,也曾發生在原住民和漢人、日本人相遇時。
下課前,請孩子們猜猜看,為什麼教科書編輯把這段也刪掉了?這天的回家作業,是請孩子們對照〈小樹〉這一課,和《少年小樹之歌》第一章的原文,找出課文還刪掉哪些段落?
再次上課時,我跟孩子們一起在白板上,做出一張表,把所有刪掉的段落列出來,請孩子們想一想,刪掉這些段落,對讀者的影響?
孩子們說:
「不知道小樹的心情,還以為他安心、冷血」
「不知道印地安人被排擠」、「歷史不要被忽略」
「不知道爺爺奶奶的心情」
「輕鬆有趣的不見了」
課文裡有一小部分傳達了爺爺奶奶對小樹的疼惜,剩下的四分之三以上篇幅,則藉著小樹的眼睛和奶奶的歌謠,述說大自然裡萬物有靈,足以撫慰人類的心,提供支持力量,這也正是一般人對原住民族的浪漫情懷。我請孩子們揣想教科書編輯的苦心,為什麼他們認為要刪掉一些「不浪漫」、暗藏衝突的段落?
「怕小孩學排擠」、「會對白人印象不好」…,孩子們提出各種可能。
待孩子們說完,我補充自己的猜想:社會上多數人認為孩子的心是「一張白紙」,要給予孩子們正向的、美好的東西。這是為什麼一般教科書裡通常只教孩子「正面的」事情。這類想法的背後,把人心看得太「扁平」了。
孩子的心靈有「複雜度」,有能力了解複雜的處境,理解「血淚」的過去,會讓情感更豐厚、更有力量。而一般老師不這麼教,可能是教師手冊裡完全沒有提到「刪改」,完全沒有列出對照表,老師如果沒空讀小說,是不會知道的。
說到這裡,一位新同學說:「我要把課本也帶回去,給以前的老師看,叫他們以後都要這樣教!」
► 吐槽課文最重要一招--文本未解的公案務必說明,不可刪
在教案討論時,一位老師提醒我,《少年小樹之歌》有個懸案:這本書後來有爭議,在美國被下架了。因為美國人民突然發現,作者曾經非常熱衷政治,甚至投入3K黨,提倡種族隔離政策。教案討論時,史英老師交代,這段公案務必要講給孩子們聽,不能「刪掉」。
孩子們聽聞公案很驚訝,不斷追問我「為什麼」?
我說明3K黨和種族隔離政策,也談到自己想了好幾天,想不明白為什麼作者會投入這些事情,這是未解的「謎」。社會上有人猜,是因為作者幹了太多壞事,所以寫這本書來「贖罪」。
說到這,孩子們紛紛開始自行解釋:
「作者就是寫出自己小時候的故事啊!」
「作者覺得自己是印地安人、但討厭黑人。」
「作者覺得身為印地安人太『弱』,要依靠『強的』(指白人)。」
「因為作者有印地安人血統,書又賣得太好,所以白人抹黑他。」
我請孩子們繼續好好研究這個懸案,以後如果有機會解開謎底,千萬別忘記,一定要回來告訴我呀!
 小何老師/森林小學老師
小何老師/森林小學老師

本文出自人本教育札記
- 相關文章推薦


2023工作報告_玩的教育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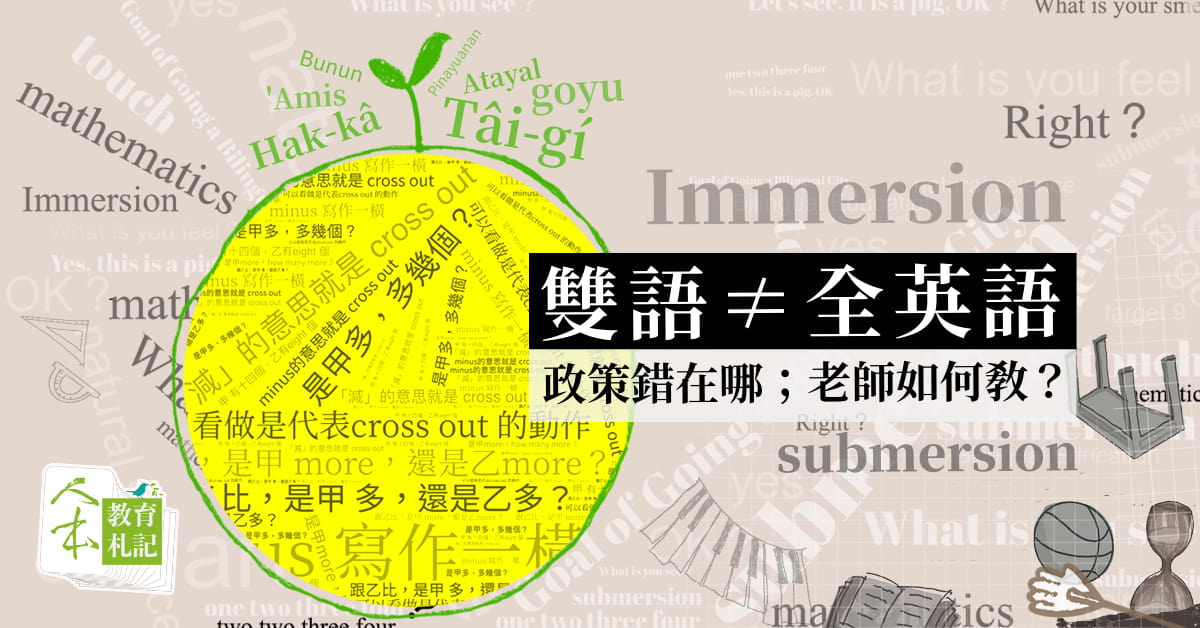
【專題】雙語 ≠ 全英語!──政策錯在哪;老師如何教?

GiveMe5 我不打小孩 家庭動起來記者會

打造愛的家,我不打小孩。台灣兒權向前行!我們可以!

快樂父母班
- 最新文章

社會賢達共同支持教育轉型正義,小英總統蒞臨人本募款餐會
人本教育基金會年度募款餐會「聚賢會」今日(10/19)順利舉行。蔡英文前總統親臨現場,與陳建仁前副總統、立法院多位委員、教育與人權倡議者、藝術家、以及公民團體代表、各界及社會賢達,共同為「教育轉型正義 全民抗網保孩」等工作籌募資金,現場氣氛熱烈,昭示教育改革信念堅定,能量持續。
曲解數據,混淆政策改善,於教育不利。全教總不要只想著廢,總該有調查監督機制吧
每年接受校事會議調查的教師,僅占不到千分之六。這樣的比例在任何工作領域中,都難以被稱為「浮濫」,反而應視為制度運作下的常態監督,是確保專業與倫理的基本機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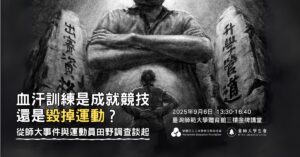
【座談會】血汗訓練是成就競技還是毀掉運動?─從師大事件與運動員田野調查談起
為深入了解台灣體育班制度下學生運動員的真實處境,人本教育基金會邀請16位曾為體育班學生,及一位現職體育班運動防護員進行焦點訪談。受訪者跨足棒球、足球、田徑、籃球等多項運動,年齡層自18歲至39歲,以呈現了體育班制度長年存在的系統性問題⋯⋯

強迫抽血惡師免解聘!?台師大血汗學分,教育部置身事外?
去年 11 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競技系教授周台英被指控於國科會「建構新世代精準女性足球運動生心理、傷害及表現的智慧感測與衡鑑平台」研究計畫中,以畢業學分強迫學生擔任受試者進行抽血、試驗,並且將受試者費收走,甚至對不願配合的學生實施精神壓力與排擠行為。現經臺師大校園霸凌調查小組認定成立周師有七項霸凌行為屬實,對三成立,建議應予以解聘,並兩年不得再擔任教師⋯⋯

請新竹、花蓮縣府不要再漠視兒少安全運動教練不適任制度也需立即建立
兒少在運動訓練過程中,遭到身心暴力,性暴力的事件頻傳。人本近期,又接到兩件申訴案。顯示不論學校外聘運動教練還是民間館場,目前教練不適任制度,仍有巨大法規漏洞,也有執行端的怠惰與混亂⋯⋯

你們挺暴力,誰來挺小孩?!校方縣府聯手放水,我們要求依法處理
本會接獲家長投訴,去年(2024年)2月他們向雲林縣西螺國中申訴廖姓專任教師與蔡姓兼任教練嚴重體罰與霸凌羽球隊學生,校方和縣府疑似輕放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