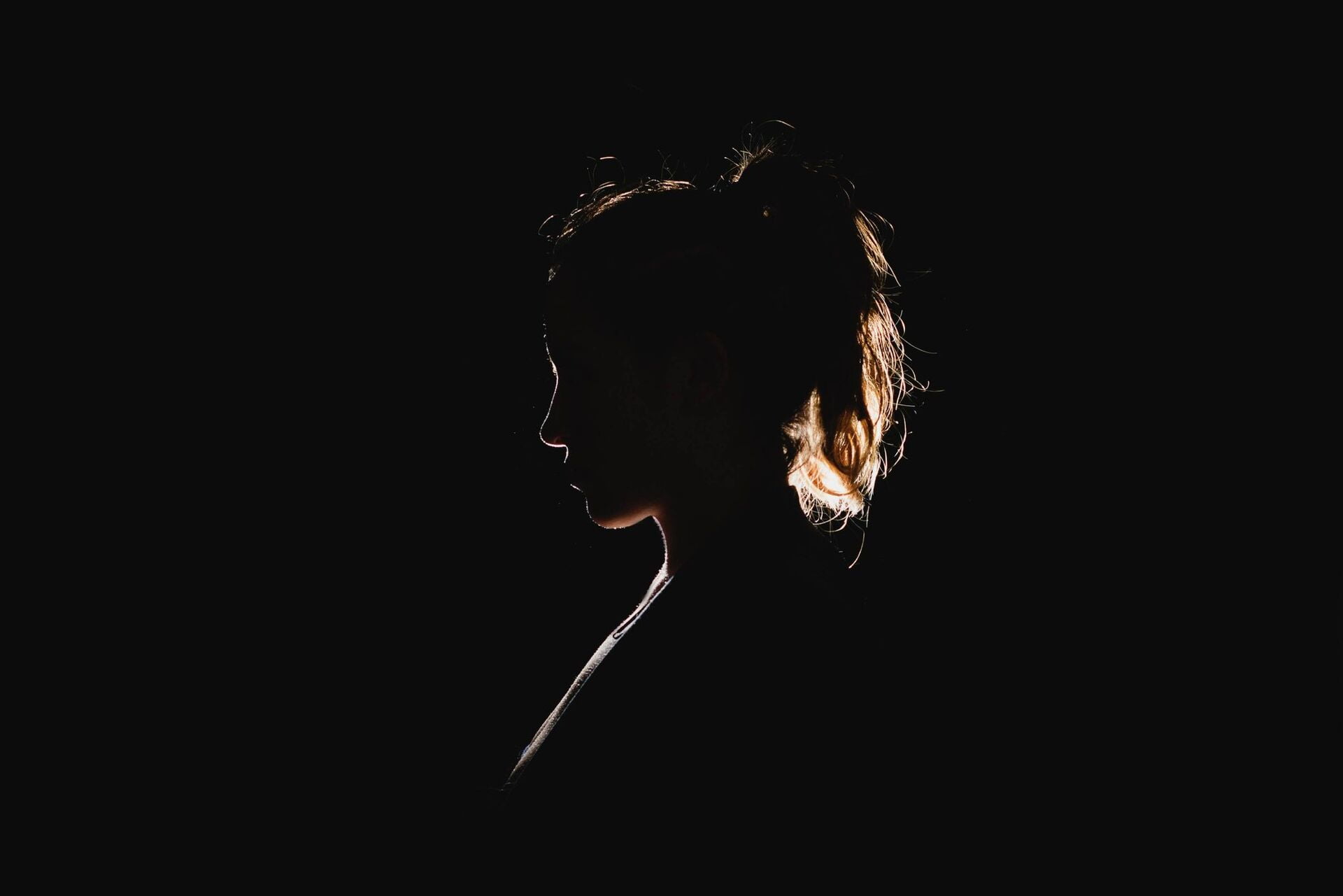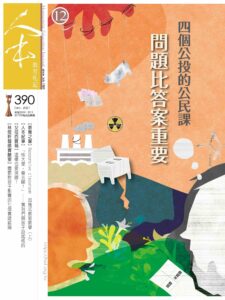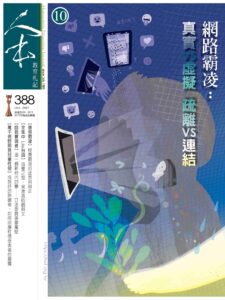如何聽懂兒童性侵受害者的求救?要耐心聆聽、給予信任 | 人本教育札記
聽懂兒童的求救:兒童性侵受害者會如何揭露

--本文刊登於人本教育札記384期
即使性侵已經結束了三十多年,潔晧回想起小時候求救的經歷,依然深刻記得當時的害怕與焦慮。
潔晧三歲時,在沒有任何溝通及通知下,被父母安排到褓姆家住。潔晧在褓姆家生活了三年,期間他被褓姆一家四口性侵。
潔晧找不到爸爸媽媽,只有自己一個人。年紀小小的他,不停尋找可以說的大人,嘗試爭取可以離開這個地方的機會。
因為生活被褓姆一家控制,要找到求救的時刻很困難。為了離開,潔晧在心裡演練千百萬次。他更下決心,即使褓姆在現場,也要說出來。
害怕與焦慮籠罩著小潔晧
沒有人知道說出來後會發生什麼事。小潔晧永遠摸不清其他成人跟褓姆的關係到底有多好。每次回想到跟媽媽說褓姆對他很壞,但媽媽卻別過頭繼續跟褓姆聊天時,小潔晧陷入極端的焦慮,不知道其他大人會否理會他。
但是生活實在太痛苦了,即使害怕成人不理會,但小潔晧也焦慮如果錯過了眼前的機會,不知道下次機會會否出現。
每次光是想到要說的時候,小潔晧身體便會有控制不到的感覺。這讓他感到很疑惑,而且更害怕。
他發現自己開始想要跟某個成人說的時候,整個身體已經在發抖,眼睛開始流下眼淚,很想說話,卻發不出幾個聲音。
四十歲的潔晧回想起這段回憶時,輕輕擦了眼淚,感嘆原來過了三十多年,這份感受依然那麼強烈而清晰。
小潔晧已經很努力了,他跟媽媽說,跟爸爸的朋友說,他試過逃離褓姆家,他試過多天不吃不喝,只是他身邊的成人沒有回應他的求救。
大部分兒童性侵受害者跟潔晧一樣,透過很多直接及間接的方法,向身邊的成人揭露。
根據挪威一份關注兒童性侵受害者如何揭露的研究,參與研究的二十名兒童性侵受害者,全部都有向身邊的成人透露受害的訊息。(註一)
兒童性侵受害者的揭露方式,跟成人不太一樣。除了直接說出性侵的經歷外,兒童及青少年也會透過暗示、行為、情緒等非直接的方式,向身邊的成人嘗試揭露。
孩子遇到性侵害後,身心會面臨非常龐大壓力。我們必須理解及體會受害孩子的心情和困境,認識兒童揭露的形式與特質,才能敏感回應孩子各種求救的訊號。
尋找願意聆聽的成人
甚少兒童性侵受害者會直接說出自己遭受性侵的經歷。
孩子對父母及身邊成人的情緒及反應非常敏感。當孩子經歷性侵害後,這份緊張及不安的感覺會加劇。特別是當加害者是家人、老師或其他長輩時,孩子被信任的成人背叛,心裡會有很多困惑難以處理。
到底誰可以信任,變得難以把握。揭露性侵需要非常謹慎。
受害者會嘗試在生活中尋找可信賴的成人,並視他們為潛在的揭露對象。然後,孩子會等待適合對話的時機。這通常是孩子與這位可信賴的成人注意力集中在孩子身上的時刻。
孩子會試探成人是否願意聆聽,是否在意自己的感受。例如學生可能會在輔導室外徘徊,找機會跟輔導老師見見面,說說同班同學的事情,或找朋友一起來坐坐閒聊。在學生對輔導老師累積了信任後,他才會開始透露性侵的訊息。
針對較年幼的兒童而言,他們較容易在主要照顧者與他們有親密接觸的時刻,例如洗澡時,說出較不含糊的揭露訊息。
試探成人態度與價值
成人的態度和價值,是性侵受害者是否揭露的重要考量。
兒童會以試探的方式,透過各種暗示,探索成人對性、性侵、親密關係、保護兒童的價值和態度,而且這些試探通常是幽微地融合在他們與成人的對話中。這些對話的主題類型很多,例如:
- 描述某人的行為(特別是他人被性侵害或性騷擾的事情)
「張老師下課後會開車載同學到他家過夜。」
「校長特別喜歡我們班上的女同學。」
「小清常常下課後被音樂老師留下來。」
- 試探你對某人或某事的看法
「你喜歡我的羽毛球教練嗎?」
「你覺得叔叔是個好人嗎?」
- 描述某人的情緒
「爺爺最近常常很生氣。」
「堂哥會突然變得很兇。」
- 給予某人給予負面評價
「舅舅對我很壞。」
「我跟阿姨一起時不舒服。」
「我不再喜歡表哥了。」
- 抗拒過往喜歡的活動
「我不想去安親班了。」
「我不想再去表哥家過夜了。」
「我一定要去學鋼琴嗎?」
- 描述一些曾參與的互動,只有簡短評論或沒有評論
「叔叔對我做了些事情。」
「鄰居哥哥跟我玩遊戲,我不喜歡。」
- 提及性侵害及性教育等相關議題
「老師今天在學校說了《蝴蝶朵朵》的故事,你知道這本繪本嗎?」
「老師說男孩子也會遇到性侵害,你相信嗎?」
- 擔憂你對他的看法
「你一定會生氣。」
「我不乖,常常都沒有做好。」
孩子是否有機會展開揭露,取決於成人與孩子對話的語調,以及成人如何延伸與兒童的對話。
如果成人的回應是封閉式的回答,例如:「不去安親班的話誰接你下課?安親班的老師很細心陪你做功課,而且我們錢都已經繳了。你長大後就不用去安親班了。」孩子會感到被拒於門外,揭露便不會發生。
若成人的回答是開放式的回答,並且提出後續提問,孩子便有機會繼續說出更多。 例如:「是喔,為什麼不想去安親班?發生什麼事嗎?」那孩子便有機會說在安親班的經歷。
孩子會非常在意成人是否願意聆聽,也會在意成人聆聽後是否承受得了。受害者如果認為聆聽的成人撐不住,例如過於憤怒或哀傷,孩子便不會進一步揭露。
透露片面資訊
在試探成人的態度與回應後,孩子可能會進一步發放更多自己遇到性侵的訊號
揭露性侵害的是一個漫長的歷程。大部分受害者在完整說出自己的性侵害經歷前,可能會經歷好幾次小型的揭露。兒童性侵受害者可能會向某些人揭露小部分的經歷,隱瞞一些信息,並依靠成人來理解他們試圖傳達的內容。
孩子透露訊息的歷程,像「擠牙膏」一樣,而且訊息的內容大多是不太直接,像是暗示。例如孩子可能會:
- 描述自己曾經歷的暴力或其他不適當對待
「叔叔打我。」
「老師不給我吃午餐。」
兒童性侵害很多時候會伴隨其他虐待兒童的行為。當兒童同時經歷多種不適當對待時,他們不一定會先說性侵害的經歷,因為每天被打或是沒有飯吃,同樣對他們的生存構成龐大的威脅。
- 輕描淡寫性侵的經歷
「叔叔親我。」
「張老師今天抱我。」
「哥哥摸我。」
「爸爸弄痛我。」
「老師對我不好。」
不同情境下,小孩淡化自己的經歷目的會不同。有些小孩會害怕自己的經歷會得到不好的回應,所以淡化自己的經歷或感受,實則是種試探。有些小孩則因為曾經歷過揭露時身心上的壓力,而本能地在敘說時不帶任何感受,才能把話說完。
向不同人發放訊號
受害孩子在尋找潛在的揭露對象時,很多時候會向不同的人發放暗示。
澳洲一名性侵受害者BCG,十七歲時被爸爸性侵多次。她爸爸是耶和華見證人(Jehovah’s Witnesses)的牧師。BCG在遭受性侵後,嘗試跟不同人揭露。她跟爸爸朋友的妻子說、她跟身兼教會長老的爸爸朋友說、也跟後來成為丈夫的男性朋友透露被性侵的資訊。
「我需要談談我和爸爸之間發生的一些事情。」
「我父親對我很粗魯。」
「我想跟你說一些你不知道的家事。關於我的父親在做的事情。」(註二)
在澳洲青少年拘留所的獨立醫護人員也發現拘留所的青年會向不同的醫護人員透露不同的資訊。醫護人員把這些不同的信息放在一起時,才會看到一個較為完整的故事。 (註三)
兒童描述性侵害經歷的用語
兒童表達及描述性侵害的方式,以及使用的用語,跟成人常用的詞彙可能有很大差異。
兒童運用的詞彙與表達的形式,會依據他們的年齡、發展階段、個人生活脈絡、以及當地文化的主流用語而有不同變化。孩子的用語也有可能是模仿加害者的形容或說法。
較年幼的兒童可能會較難以成人常用的術語描述性虐待,但這不代表幼兒無法描述。
蘇格蘭一份關注兒童如何描述性侵害經歷的研究,分析2986位兒童在致電當地「兒童熱線」(ChildLine)時揭露性侵害的對話內容,發現5至18歲的兒童及青少年均可以清楚地描述性侵害的經歷及感受。(註四)
根據這份蘇格蘭「兒童熱線」的研究顯示,許多兒童會運用「性虐待」(sexual abuse)、「強暴」(rape)、 「陰莖」(penis) 、「陰道」(vagina)等名詞和術語來描述他們的經歷。10至14歲的青少年會較常用「隱私部位」(private parts)、「隱私處」(private places)、「私處」等詞彙。這代表這些兒童及青少年具備對性及身體的知識,對性侵害也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並知道如何運用成人能理解的術語來溝通。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兒童運用了兒童性侵害相關的術語,也有可能與他們的經歷並不相稱的狀況。例如有些孩子用「性騷擾」來形容肛交等形式的性虐待。
「爸爸最近在性騷擾我。昨天他把某東西插進我的後面。」(註五)
孩子也可能用「強暴」一詞,來涵蓋身體被不適當觸碰的經歷。
「叔叔住在我家一個星期了。晚上他都會來我的房間強暴我。他會脫褲子,然後摸我的上面。」除了運用與「性」或「性侵」明顯相關的詞彙,很多孩子會以委婉的說法,來描述性互動的行為。
「摸」是孩子常用的描述。儘管「摸」這動作,不能明確肯定孩子是否經歷不適當對待,但成人也不能掉以輕心。若成人回小孩說:「摸一下又沒怎樣,不要那麼大驚小怪,老師喜歡你才會摸你。」,我們很可能會錯過孩子的求救訊號。
揭露性侵是非常有壓力的事情。受害者在描述性侵害經歷的同時,身心會伴隨極度恐慌、害怕、絕望的感受。很多受害孩子會感到直接描述會太恐怖,身心會負荷不了,所以選擇比較「含糊」的詞彙時,事情感覺沒那麼嚴重,身心會比較能夠承受。
再加上我們日常生活中不常談論性侵及性互動等主題,孩子可能會選擇相對「無害」、較容易說出口的詞彙來描述身體部位,例如:雞雞、妹妹、屁屁、下面、中間、後面、那個,感覺不會那麼尷尬。
「叔叔一直撫摸我中間的地方。」、「他的手指在我的中間那邊。」一名六歲女孩的陳述。(註六)
我們要注意,孩子把事情說得很輕微時,不等於事情不嚴重。孩子說出很嚴重的指控時,我們也要耐心確認實際發生的事情,因為孩子即使運用了某些專有名詞,例如性侵害,但可能並不確定這詞彙真正的內涵。
透過行為及情緒表達的非直接揭露
很多兒童性侵受害者會透過非語言的方式揭露性侵,特別是學齡前及學齡兒童,大多會透過行為、情緒反應或無心的描述,不經意地揭露性侵害的事情。
孩子可能會表示不喜歡某人、不想見到對方、對某人表示不滿、拒絕與某人見面或共處。
青少年也會運用非直接的方式揭露,然而表達的方式會跟年幼兒童不一樣。青少年可能會以自殘的方式,例如割手腕、拔頭髮,向身邊的成人發出求救信號。(註七)有些青少年會忽略自己肚餓的感覺,餓了也不吃東西。
部分青少年會讓自己感官過載,例如聆聽非常高音量的音樂、持續打電動、即使疲累也不休息。這種看似無法控制的上癮的行為,很多時候是受害者短暫脫離現實痛苦的存活策略。
部分青少年為了避免成人評價他們的選擇,不想成人介入他們的生活,所以選擇對遇到性侵害的事情一字不提。
遭遇性侵害後,受害者可能會被龐大的無力感所籠罩。受害者感到自己無法改變任何事情,所以使用最消極的方法來回應任何關係。青少年可能會變得沉默寡言,對生活、家人、學習呈現極度抽離的狀態。
這種拒絕、沉默、漠不關心的態度與行為,是青少年遭受性虐待後,嘗試取回自己生活主控權的其中一種努力,也是他們以非直接的方式,揭露自己的痛苦。
如果有人對青少年的消極,持續給予溫暖的回應,會有助與青少年慢慢建立信任,並展開進一步的溝通。
當孩子否認與撤回揭露
否認與撤回揭露,是指受害者撤消先前對性虐待的指控。
儘管部分兒童在揭露性侵害的經歷後,突然撤消先前作出的控訴,並不一定代表性侵害沒有發生。 很多撤回性侵指控的兒童,後來都會再次確認先前的揭露。
孩子的生活與人際關係,會因為揭露性侵害而發生一連串改變。這些變動大部分不是受害者可以預期和控制的。
加害者的壓力和威脅、警察及司法程序的詢問和調查、不想再重複述說、擔憂家人的情緒,都是孩子撤回性侵害指控的普遍原因。
眾多研究指出兒童很少會作出虛假的性侵害指控。(註八)成人應該要意識到即使孩子撤回了性侵害的陳述,或否認遇到性侵害,但這不代表性侵害沒有發生。我們要關注孩子是否正承受極大壓力,不得不保持沉默。
若孩子隨後再次肯定之前的說法,或是揭露更多的經歷,成人必須要耐心聆聽,給予信任,並不可以指責孩子早前曾經否認。
成人的責任
性侵加害者會利用多種手段,控制孩子保持沉默。受害者揭露性侵經歷時,會面臨很多阻礙。
我們不應假定孩子遭遇性虐待後,會向主動向父母或老師揭露。我們也不能假定孩子會以清晰明瞭的語言揭露。性侵受害者已經面臨很多痛苦和身心壓力,我們不應該給予受害者更多的負擔。
反之,社會每一位不同身分的成人,應該一起理解兒童性侵害,關注身邊孩子的行為變化,細心聆聽孩子試圖說出的話,並創造友善的條件與空間,支持受害者安全地進行揭露。
註一:Flåm, A. M. & Haugstvedt, E. (2013). Test balloons? Small signs of big events: A qualitative study on circumstances facilitating adults’ awareness of children’s first signs of sexual abuse.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37: 633-642.
註二: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Report of Case Study 29: The response of the Jehovah’s Witnesses and Watchtower Bible and Tract Society of Australia Ltd to allegations of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 31
註三: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Volume 4: Identifying and disclosing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 52.
註四:蘇格蘭的「兒童熱線」是一個免付費的保密電話諮詢服務。 Jackson, S., Newall, E., & Backett‐Milburn, K. (2013). Children’s narratives of sexual abuse. Child and Family Social Work, 20(3), 322-332.
註五:Jackson, S., Newall, E., & Backett‐Milburn, K. (2013). Children’s narratives of sexual abuse. Child and Family Social Work, 20(3), p. 327.
註六:Jackson, S., Newall, E., & Backett‐Milburn, K. (2013). Children’s narratives of sexual abuse. Child and Family Social Work, 20(3), p. 327.
註七:Ungar, M,. Barter, K. McConnell, S. M., Tutty, L. M. & Fairholm, J. (2009). Patterns of abuse disclosure among youth. Qualitative Social Work, 8(3): p. 352.
註八: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Volume 4: Identifying and disclosing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 53.
【參考文獻】
Flåm, A. M. & Haugstvedt, E. (2013). Test balloons? Small signs of big events: A qualitative study on circumstances facilitating adults’ awareness of children’s first signs of sexual abuse.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37: 633-642.
Jackson, S., Newall, E., & Backett‐Milburn, K. (2013). Children’s narratives of sexual abuse. Child and Family Social Work, 20(3), 322-332.
Reitsema, A. M., & Grietens, H. (2016). Is anybody listening? The literature on the dialogical process of child sexual abuse disclosure reviewed. Trauma, Violence, & Abuse, 17(3), 330–340.
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Volume 4: Identifying and disclosing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Ungar, M,. Barter, K. McConnell, S. M., Tutty, L. M. & Fairholm, J. (2009). Patterns of abuse disclosure among youth. Qualitative Social Work, 8(3): 343.
- 主編精選